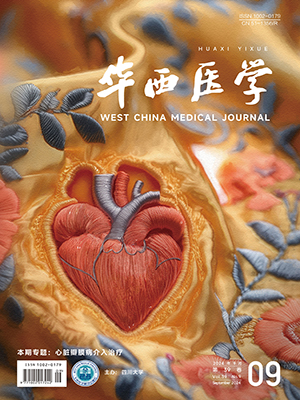引用本文: 张羽, 白云金, 唐寅, 王佳, 魏武然. 经皮肾镜取石术不同入路对完全鹿角形肾结石疗效的影响. 华西医学, 2021, 36(8): 1068-1071. doi: 10.7507/1002-0179.202001005 复制
鹿角形肾结石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肾结石,具有结石复杂、取石困难、手术难度大以及术后结石容易复发的特点,是上尿路结石治疗的难点和重点,而填满所有肾盏和肾盂的完全性结石的治疗更具有挑战性。经皮肾镜取石术(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PCNL)是完全鹿角形肾结石治疗的主要措施,而手术入路选择至关重要,关系到手术安全性、清石率等,国内外学者针对鹿角形肾结石 PCNL 的入路展开了多项研究和分析,其结果尚无定论[1-4]。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由同一术者行单通道 PCNL 治疗的完全鹿角形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比较经肾上盏、中盏和下盏入路的 PCNL 治疗完全鹿角形肾结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选择 2009 年 10 月—2019 年 8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由同一术者行单通道 PCNL 术的完全鹿角形肾结石患者。纳入标准(全部满足):经腹部平片(kidney-ureter-bladder,KUB)或 CT 确诊为完全鹿角形肾结石;首次建立通道;同侧肾只建立 1 条经皮肾通道;由同一术者行手术。排除标准(满足任意一项):年龄<16 周岁;凝血系统障碍;肝功能异常;未经严格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免疫系统疾病者;近 6 个月内有过心脑血管意外事件;近 3 个月内泌尿系统严重感染史且有症状。剔除标准:患者数据不全时,将其剔除该组的统计分析。本研究已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2020 年审(96)号。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组
根据 PCNL 手术入路不同,分为上盏入路组、下盏入路组和中盏入路组。
1.2.2 治疗方法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截石位,经尿道膀胱镜下插入 6Fr 输尿管插管,再取俯卧位常规消毒铺巾,经输尿管插管往肾盂注入造影剂后,在 X 线定位下根据术中造影、术前腹部 CT 及腹部平片选择合适的穿刺入路进行穿刺、扩张,置入 24Fr 工作鞘,经鞘入镜,交替使用超声、钬激光和气压弹道碎石并逐步取出结石,术毕留置 6Fr 输尿管支架、肾造瘘管和尿管各 1 根。
1.2.3 评价标准
根据文献[5]的建议,PCNL 术后结石残余物直径≤4 mm 且上尿路解剖正常的情况下认为结石被完全清除,否则为有残石。清石时间是指从经皮介入通道建立完成开始到留置肾造瘘管完成的时间。患者术后 2 d 内出现体温高于 38℃ 则记录为发热,若高于 39.1℃ 则记录为高热。若患者出现需要使用药物或其他临床手段干预(如夹闭肾造瘘管、血管介入栓塞止血等)的出血则记录为术后出血。
1.3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糖尿病史、高血压史、肾脏病史及结石尺寸等临床资料。统计 3 组患者术后第 1 天影像评估的即时结石清除率(结石清除率=术后无残石患者数/结石清除结果未缺失患者总数×100%),记录 3 组患者的清石时间、术后发热、出血及胸膜损伤的发生情况,并记录仅行一期手术患者术后至拔管的天数。并发症依据 Clavien 分级法[6]进行分级。结石体积根据文献[5],取其计算公式为 0.6×结石表面积1.27;其中,结石表面积=结石的长×结石的宽×π×0.2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型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F 检验。二分类变量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双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共纳入 379 例患者。其中,上盏入路组 146 例,下盏入路组 170 例,中盏入路组 63 例。3 组患者除年龄外,性别、BMI、结石体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379 例患者中,无术前合并症 37 例,术前合并症资料缺失 83 例。术前合并症包括独肾 36 例、肾脏解剖畸形 5 例、糖尿病 20 例、尿培养阳性 96 例、脓苔 32 例、高血压 57 例、肾积水 149 例、蛋白尿 199 例、肉眼血尿 50 例。3 组患者术前合并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2.2 患者术后资料统计
379 例患者中,术后清石资料缺失 5 例,术后并发症资料缺失 83 例,无残石 137 例,发热 77 例,出血 11 例,胸膜损伤 8 例。见表 3。
3 组 374 例患者的清石率为 36.63%(137/374),清石时间为(47.02±19.38)min,术后发热率为 26.01%(77/296),术后出血发生率为 3.72%(11/296)。仅行一期手术的 215 例患者(上盏入路组 80 例,下盏入路组 112 例,中盏入路组 23 例)的拔管天数为(7.02±3.97)d。除 1 例患者行血管介入栓塞止血(Clavien 分级Ⅱ级)外,未见高热、输血、尿脓毒症等其他 Clavien 分级Ⅱ级及以上的术后并发症。3 组患者的清石时间、拔管天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清石率、术后发热率、术后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3 组患者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但有文献指出年龄对 PCNL 疗效几乎无影响[7],因此我们判断各组间患者具有可比性。理论上讲,由于肾脏的解剖特性,上盏入路使经皮肾镜发生扭曲的可能性降低,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平行于肾脏长轴的进镜通路,从而提高了镜下探测和粉碎结石的效率,也可最大程度地降低肾脏机械性损伤的风险[8]。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清石率方面,虽然上盏入路具有相对更高的清石率,然而 3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7)。我们认为,这可能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数据的回顾性分析,难免会有选择偏倚或其他混杂偏倚的存在,且研究的样本量并不大,因此造成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经过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目前对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清石率的报道非常少,多数都是合并在鹿角形肾结石清石研究中。
目前对于 PCNL 穿刺入路的选择并无权威的指导标准,但我们在评估患者穿刺入路的选择时,遵循了以下的原则:首先,根据肾脏与周围脏器的毗邻关系,排除不合适的入路以尽可能降低损伤周围脏器的可能性;其次,穿刺入路的选择应保障肾镜在操作过程中对肾脏的机械损伤最小的同时,可到达尽可能多的肾盏;另外,对于输尿管上段结石或术中碎石可能落入输尿管的患者,应优先考虑肾镜更容易抵达输尿管的上盏或中盏入路,以提高处理结石的效率。
上盏入路可能也使患者面临更高的胸膜损伤风险,我们观察到上盏入路术后有 8 例胸膜损伤。胸膜损伤常与解剖变异,较低的 BMI 及穿刺的熟练程度和手法等直接相关[9],虽少见,但却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因此也应引起重视。一般来说,如穿刺位点位于第 12 肋以上,则胸膜和肺部受损的风险会增高,使用超声控制穿刺或呼气时穿刺也可一定程度上预防胸膜损伤[10-11]。这将是未来前瞻性研究重点关注的术后并发症之一。
由于 PCNL 本身的特点,出血是该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本研究患者总体出血发生率为 3.72%,其中仅 1 例因出血而采用了血管介入栓塞治疗,无输血病例。大量出血的原因或许与穿刺手法有关,如损伤肾门血管,同时也可能因为造成假性动脉瘤或动静脉瘘而造成迟发性出血。另外,由穿刺后引入导丝的过程中所致的肾盂穿孔也可致严重的出血,有文献报道其发生率高达 7.2%[12]。在美国和英国,肾脏通路通常由放射科医生建立,在一些欧洲国家,泌尿科医生使用超声/荧光镜,系统扫描仪或半导体扫描仪等系统来引导穿刺,这种方法可更准确地确定肾脏长轴,从而确保穿刺针的正确定位[13]。
除出血外,发热也是鹿角形肾结石患者 PCNL 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由于鹿角形肾结石通常含有磷酸铵镁石和(或)碳酸钙/磷灰石成分,与尿路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结石负荷量大,手术时间相对较长,碎石过程中容易造成毒素和致热源的吸收。本研究中发热的发生率为 26.01%。文献报道高热的发生率为 0.8%~4.7%[14]。术前尿培养阳性、肾功能不全、手术时间过长或灌注液用量过多以及集合系统内压力过高均是术后发生高热或感染的高危因素[6, 15-17]。术前应对这些患者根据药物敏感性试验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5]。对于严重感染所致的尿脓毒症,不同的文献所记载的发生率则不尽相同,为 0.97%~4.8%[14, 17]。本研究中无高热、尿脓毒症患者,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预防性抗菌药物使用越来越规范。
目前,国内对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患者不同通路 PCNL 疗效观察的回顾性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为未来在此领域设计和实施前瞻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以往在此领域的研究,不论是回顾性的还是前瞻性的,均未将患者限定至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而其位置和形状的不同,正是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我们通过筛选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来避免结石的位置和其与肾盂形状的关系不同造成的混杂偏倚。
当然,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如前所述,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因此无可避免地会存在选择偏倚和混杂偏倚。另外,由于患者资料的时间跨度较大,术者手术的熟练度、器械的更新等都可能对手术的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同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一些特殊解剖情况的患者,如马蹄肾、重复肾、肾盂输尿管狭窄、盏颈口狭窄、肾旋转不良和肾囊肿等可能影响手术的患者未被排除在统计外。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意降低这类混杂因素的影响。
鹿角形肾结石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肾结石,具有结石复杂、取石困难、手术难度大以及术后结石容易复发的特点,是上尿路结石治疗的难点和重点,而填满所有肾盏和肾盂的完全性结石的治疗更具有挑战性。经皮肾镜取石术(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PCNL)是完全鹿角形肾结石治疗的主要措施,而手术入路选择至关重要,关系到手术安全性、清石率等,国内外学者针对鹿角形肾结石 PCNL 的入路展开了多项研究和分析,其结果尚无定论[1-4]。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由同一术者行单通道 PCNL 治疗的完全鹿角形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比较经肾上盏、中盏和下盏入路的 PCNL 治疗完全鹿角形肾结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选择 2009 年 10 月—2019 年 8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由同一术者行单通道 PCNL 术的完全鹿角形肾结石患者。纳入标准(全部满足):经腹部平片(kidney-ureter-bladder,KUB)或 CT 确诊为完全鹿角形肾结石;首次建立通道;同侧肾只建立 1 条经皮肾通道;由同一术者行手术。排除标准(满足任意一项):年龄<16 周岁;凝血系统障碍;肝功能异常;未经严格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免疫系统疾病者;近 6 个月内有过心脑血管意外事件;近 3 个月内泌尿系统严重感染史且有症状。剔除标准:患者数据不全时,将其剔除该组的统计分析。本研究已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2020 年审(96)号。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组
根据 PCNL 手术入路不同,分为上盏入路组、下盏入路组和中盏入路组。
1.2.2 治疗方法
麻醉成功后患者取截石位,经尿道膀胱镜下插入 6Fr 输尿管插管,再取俯卧位常规消毒铺巾,经输尿管插管往肾盂注入造影剂后,在 X 线定位下根据术中造影、术前腹部 CT 及腹部平片选择合适的穿刺入路进行穿刺、扩张,置入 24Fr 工作鞘,经鞘入镜,交替使用超声、钬激光和气压弹道碎石并逐步取出结石,术毕留置 6Fr 输尿管支架、肾造瘘管和尿管各 1 根。
1.2.3 评价标准
根据文献[5]的建议,PCNL 术后结石残余物直径≤4 mm 且上尿路解剖正常的情况下认为结石被完全清除,否则为有残石。清石时间是指从经皮介入通道建立完成开始到留置肾造瘘管完成的时间。患者术后 2 d 内出现体温高于 38℃ 则记录为发热,若高于 39.1℃ 则记录为高热。若患者出现需要使用药物或其他临床手段干预(如夹闭肾造瘘管、血管介入栓塞止血等)的出血则记录为术后出血。
1.3 观察指标
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糖尿病史、高血压史、肾脏病史及结石尺寸等临床资料。统计 3 组患者术后第 1 天影像评估的即时结石清除率(结石清除率=术后无残石患者数/结石清除结果未缺失患者总数×100%),记录 3 组患者的清石时间、术后发热、出血及胸膜损伤的发生情况,并记录仅行一期手术患者术后至拔管的天数。并发症依据 Clavien 分级法[6]进行分级。结石体积根据文献[5],取其计算公式为 0.6×结石表面积1.27;其中,结石表面积=结石的长×结石的宽×π×0.2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型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F 检验。二分类变量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双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共纳入 379 例患者。其中,上盏入路组 146 例,下盏入路组 170 例,中盏入路组 63 例。3 组患者除年龄外,性别、BMI、结石体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379 例患者中,无术前合并症 37 例,术前合并症资料缺失 83 例。术前合并症包括独肾 36 例、肾脏解剖畸形 5 例、糖尿病 20 例、尿培养阳性 96 例、脓苔 32 例、高血压 57 例、肾积水 149 例、蛋白尿 199 例、肉眼血尿 50 例。3 组患者术前合并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2.2 患者术后资料统计
379 例患者中,术后清石资料缺失 5 例,术后并发症资料缺失 83 例,无残石 137 例,发热 77 例,出血 11 例,胸膜损伤 8 例。见表 3。
3 组 374 例患者的清石率为 36.63%(137/374),清石时间为(47.02±19.38)min,术后发热率为 26.01%(77/296),术后出血发生率为 3.72%(11/296)。仅行一期手术的 215 例患者(上盏入路组 80 例,下盏入路组 112 例,中盏入路组 23 例)的拔管天数为(7.02±3.97)d。除 1 例患者行血管介入栓塞止血(Clavien 分级Ⅱ级)外,未见高热、输血、尿脓毒症等其他 Clavien 分级Ⅱ级及以上的术后并发症。3 组患者的清石时间、拔管天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清石率、术后发热率、术后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3 组患者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但有文献指出年龄对 PCNL 疗效几乎无影响[7],因此我们判断各组间患者具有可比性。理论上讲,由于肾脏的解剖特性,上盏入路使经皮肾镜发生扭曲的可能性降低,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平行于肾脏长轴的进镜通路,从而提高了镜下探测和粉碎结石的效率,也可最大程度地降低肾脏机械性损伤的风险[8]。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清石率方面,虽然上盏入路具有相对更高的清石率,然而 3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7)。我们认为,这可能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数据的回顾性分析,难免会有选择偏倚或其他混杂偏倚的存在,且研究的样本量并不大,因此造成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经过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目前对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清石率的报道非常少,多数都是合并在鹿角形肾结石清石研究中。
目前对于 PCNL 穿刺入路的选择并无权威的指导标准,但我们在评估患者穿刺入路的选择时,遵循了以下的原则:首先,根据肾脏与周围脏器的毗邻关系,排除不合适的入路以尽可能降低损伤周围脏器的可能性;其次,穿刺入路的选择应保障肾镜在操作过程中对肾脏的机械损伤最小的同时,可到达尽可能多的肾盏;另外,对于输尿管上段结石或术中碎石可能落入输尿管的患者,应优先考虑肾镜更容易抵达输尿管的上盏或中盏入路,以提高处理结石的效率。
上盏入路可能也使患者面临更高的胸膜损伤风险,我们观察到上盏入路术后有 8 例胸膜损伤。胸膜损伤常与解剖变异,较低的 BMI 及穿刺的熟练程度和手法等直接相关[9],虽少见,但却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因此也应引起重视。一般来说,如穿刺位点位于第 12 肋以上,则胸膜和肺部受损的风险会增高,使用超声控制穿刺或呼气时穿刺也可一定程度上预防胸膜损伤[10-11]。这将是未来前瞻性研究重点关注的术后并发症之一。
由于 PCNL 本身的特点,出血是该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本研究患者总体出血发生率为 3.72%,其中仅 1 例因出血而采用了血管介入栓塞治疗,无输血病例。大量出血的原因或许与穿刺手法有关,如损伤肾门血管,同时也可能因为造成假性动脉瘤或动静脉瘘而造成迟发性出血。另外,由穿刺后引入导丝的过程中所致的肾盂穿孔也可致严重的出血,有文献报道其发生率高达 7.2%[12]。在美国和英国,肾脏通路通常由放射科医生建立,在一些欧洲国家,泌尿科医生使用超声/荧光镜,系统扫描仪或半导体扫描仪等系统来引导穿刺,这种方法可更准确地确定肾脏长轴,从而确保穿刺针的正确定位[13]。
除出血外,发热也是鹿角形肾结石患者 PCNL 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由于鹿角形肾结石通常含有磷酸铵镁石和(或)碳酸钙/磷灰石成分,与尿路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结石负荷量大,手术时间相对较长,碎石过程中容易造成毒素和致热源的吸收。本研究中发热的发生率为 26.01%。文献报道高热的发生率为 0.8%~4.7%[14]。术前尿培养阳性、肾功能不全、手术时间过长或灌注液用量过多以及集合系统内压力过高均是术后发生高热或感染的高危因素[6, 15-17]。术前应对这些患者根据药物敏感性试验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5]。对于严重感染所致的尿脓毒症,不同的文献所记载的发生率则不尽相同,为 0.97%~4.8%[14, 17]。本研究中无高热、尿脓毒症患者,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预防性抗菌药物使用越来越规范。
目前,国内对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患者不同通路 PCNL 疗效观察的回顾性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为未来在此领域设计和实施前瞻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以往在此领域的研究,不论是回顾性的还是前瞻性的,均未将患者限定至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而其位置和形状的不同,正是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我们通过筛选完全性鹿角形肾结石,来避免结石的位置和其与肾盂形状的关系不同造成的混杂偏倚。
当然,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如前所述,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因此无可避免地会存在选择偏倚和混杂偏倚。另外,由于患者资料的时间跨度较大,术者手术的熟练度、器械的更新等都可能对手术的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同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一些特殊解剖情况的患者,如马蹄肾、重复肾、肾盂输尿管狭窄、盏颈口狭窄、肾旋转不良和肾囊肿等可能影响手术的患者未被排除在统计外。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意降低这类混杂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