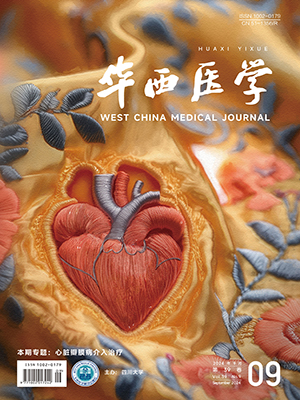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常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机制复杂,以对称性多关节肿痛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诊疗有助于 RA 患者预后。目前,RA 诊疗仍面临重大挑战,迫切需要创新模式以提高早期诊断和高效治疗的能力。医工结合作为一种创新交叉研究模式,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展现出良好的前景,有望改善基于传统 RA 诊疗的需求和不足。该文就近年来医工结合新技术在 RA 诊疗领域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拓展 RA 精准诊疗的新思路。
引用本文: 朱笔挥, 王丽芸, 容逍, 邱逦. 类风湿关节炎医工结合诊疗的研究进展. 华西医学, 2024, 39(10): 1650-1656. doi: 10.7507/1002-0179.202404014 复制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种常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全球发病率为 0.5%~1%,30~60 岁女性最常见[1]。RA 以对称性多关节疼痛和肿胀为主要特征,可累及全身多个大小关节,表现为滑膜增生、新生血管生成、进行性软骨损伤、骨侵蚀和关节畸形[2]。此外,RA 可引起关节外器官并发症,如贫血、肺间质性病变、心肌梗死、脑卒中等,最终导致严重的功能退化而致终身残疾,预期寿命明显降低,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3]。目前,RA 诊疗仍面临着重大挑战,迫切需要创新模式以提高早期诊断和高效治疗的能力。医工结合是多学科融合的领域,旨在通过工程技术的创新应用解决医学领域面临的挑战,包括生物医学检测、生物医学材料、医疗人工智能等多个新兴领域,有利于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4-5]。然而,该领域在 RA 诊断与治疗应用方面缺乏系统综述。因此,本文就近年来医工结合新技术在 RA 诊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拓展 RA 诊疗的新思路。
1 基于 RA 诊疗需求的医工结合
RA 发病机制错综复杂,存在遗传因素、环境暴露和免疫系统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涉及多种免疫细胞(如 T 细胞、B 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巨噬细胞等)以及非免疫细胞(如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等),它们在疾病持续进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7]。炎症反应是 RA 发病的核心,多种免疫细胞、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形成交织的正反馈通路。研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处于炎性细胞因子级联反应的顶端,驱动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1β和 IL-6 的表达。RA 骨免疫代谢同时受炎症因子和骨代谢效应细胞调控[8],炎症因子刺激下游滑膜细胞、破骨细胞等效应细胞导致滑膜组织过度增生从而破坏骨代谢动态平衡,是破坏关节的病理基础。此外,RA 滑膜组织呈“肿瘤样”过度增生时会诱导局部组织缺氧、血管通透性增加并刺激新生血管生成,同时,炎症微环境中存在高水平一氧化氮、活性氮及活性氧,其与炎症反应相互作用,导致细胞突变、遗传毒性和基因组大量缺失,促进疾病进展,最终在 RA 晚期刺激破骨细胞降解骨基质、溶解骨钙从而发生骨侵蚀[1, 3]。
由于 RA 是一种或多种共存条件以及关节外表现相关的全身性疾病,疾病呈连续的过程,起源于无症状的免疫功能障碍,并在关节症状之前经历不同阶段,因此其疾病机制也可能随着疾病的不同阶段而变化[2]。RA 早期滑膜成纤维细胞的表观遗传标记与疾病晚期的表观遗传标记有很大不同,抗瓜氨酸蛋白抗体(anti 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 ACPA)的特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9]。因此,RA 诊疗策略强调在疾病早期进行更积极的干预[10]。
现有 RA 诊断方法主要通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与影像学评估相结合。2010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和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提出新的 RA 分类标准和评分系统,其中 ACPA、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s, RF)、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有助于 RA 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11]。其中,ACPA 是疾病早期发现的主要内源性抗体,对预测关节侵蚀具有更高价值,然而其虽然特异度较高,可达到 90%,灵敏度只有 50%~75%;RF 作为 RA 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其阳性率为 75%~80%,当呈高滴度阳性时可提示患者关节炎症状的严重程度,但还可见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或非感染性疾病;CRP 和 ESR 也可用于 RA 诊断,但均为非特异性炎症因子,主要用于评估机体疾病活动度[12]。RA 诊断的影像学技术包括 X 线、CT、MRI 和肌骨超声。X 线片和 CT 在评估关节结构损害具有优势,但软组织分辨率差,难以显示疾病初期滑膜炎等病变;MRI 和超声是评估早期关节炎最主要的成像技术,然而 MRI 特异性低且成本高昂从而限制临床应用,超声具有便捷、可重复性、无创性等优点,能够实时动态地诊断及监测疗效[13]。尽管影像学发展至今对 RA 诊断日趋成熟,但由于早期 RA 症状不明显,导致影像学技术仍然对其检出受限。因此,提高 RA 血清学标志物以及影像学技术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是早期诊断 RA 的关键。
目前 RA 的临床治疗目标包括改善病情、缓解关节肿痛并且抑制滑膜炎、防止疾病的发展、预防关节软骨损伤和骨侵蚀从而保护关节的整体功能,其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 GC)、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 DMARD)、生物制剂及靶向药物[14]。GC 能够快速减轻关节炎症状,被广泛应用于早期和活动期 RA,系统性使用 GC 能够达到改善病情的目的,延缓病情的发展,防止关节损伤;然而长期或者大剂量使用 GC 会加重感染风险,特别是对老年患者,其不良反应中骨质疏松和感染最常见。NSAID 具有良好的抗炎和解热镇痛作用,尽管它们广泛用于缓解症状,但不能减缓 RA 的病情发展,同时 NSAID 的使用也会产生肠胃不适、消化道溃疡、急性肾功能损伤以及心血管问题等不良反应。DMARD 作为治疗 RA 的一线用药,通常耐受性良好,其目的在于早期缓解关节炎症状,降低骨和软骨破坏,阻止疾病的发展[15-16]。根据 RA 的严重程度、患者的耐受程度和并发症,DMARD 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药物联用达到更好疗效。生物制剂近年来发展迅速,其主要通过阻断疾病过程中的关键炎症细胞因子或细胞表面分子而发挥治疗作用,如 TNF-α抑制剂、IL-6 抑制剂、IL-1 受体拮抗剂、T 细胞抑制剂和诱导 B 细胞凋亡单克隆抗体(CD20 单抗)等。上述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但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然需要改进,长期的药物使用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也体现在非靶器官、组织及细胞上,如胃肠道症状、免疫抑制、感染和新生肿瘤等。因此,寻找针对 RA 治疗的创新策略从而减少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医工结合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医工结合将临床医学的迫切需求和先进的工程技术手段相融合,解决了许多临床医学的难点及痛点,不仅推动了新型医学诊疗技术的研发,还加速了智能医疗与健康管理的创新,从而提升了临床诊疗水平,并实现医疗服务的革命性提升。在 RA 诊断与治疗方面,医工结合也具有巨大潜力,例如利用微纳米技术开发生物传感器或结合纳米探针开发分子影像技术用于 RA 精准诊断,应用多模态新型成像技术定量评估 RA 活动度,设计纳米生物材料作为载体或仿生药物实现 RA 靶向分子水平治疗等。因此,医工结合的突破和创新有望改善基于传统 RA 诊疗的需求和不足。
2 医工结合应用于 RA 诊断
2.1 生物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是由生物敏感材料识别系统和理化换能器结合的分析工具,生物元件固定在固态表面上,与目标分析物进行特异性作用,最后将生化响应转换为可测量的输出信号[17]。生物传感器的开发实现了在单一平台上快速、特异性筛选生物标志物的可能,并提升了检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是帮助早期诊断疾病的重要工具,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新型生物传感器技术还可以利用高度个性化的诊断、便携化检测和实时监测改善 RA 患者的诊疗体验。目前,针对 RA 的生物传感器主要集中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和光学生物传感器[19-22]。
ACPA 和 RF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诊断 RA 的生物标志物。有研究设计一种能够同时测定 RF 和 ACPA 的简便、快速的双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其结果显示,该传感器对 RF 和 ACPA 均具有很高的灵敏度[23]。此外,该生物传感器还具有很强的选择性;2个靶标的定量检测可在 2 h 内同时完成,而所需样品体积仅需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的 1/4[23]。对比传统单独检测方法,该多重生物传感器具有更高的检测效率,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随后有研究利用各向异性有机-无机杂化纳米颗粒独特的光学特性制备了各向异性双金属聚合物纳米簇来作为光学免疫生物传感器;作为基于表面增强拉曼散射信号的纳米探针,其通过抗原-抗体相互作用定量分析 RF 和 ACPA 2 种 RA 生物标志物,证明了生物标志物浓度与拉曼强度之间的定量关系,且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在低浓度范围也可显示拉曼强度;由于快速和高灵敏度的检测能力,该新型多重光学生物传感器可替代商业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满足当前对 RA 早期诊断的需求[24]。
2.2 光声成像(photoacoustic imaging, PAI)
PAI 是一种混合成像技术,在可调节的电磁波长范围内发射激光并接收超声信号以形成图像,目标信号的强度与光吸收量成正比。PAI 结合了光学成像和超声成像的优势,同时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和深穿透度的特点,可以在多个波长下观察到人体内的固有物质,包括氧合和脱氧血红蛋白、黑色素、水、脂质等[25-26]。PAI 能够在可见光谱范围内定量氧化和脱氧血红蛋白,也可以测量血红蛋白的一些功能指标,同时实现形态和功能成像;此外,外源性光学纳米载体的出现使 PAI 在分子成像方面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及药物递送的监测。由于 PAI 的多功能成像特点,其作为一种创新的光学成像技术已被逐渐应用在实验动物和临床研究中,包括关节成像领域[27-29]。
组织缺氧会引发异常免疫细胞的激活和增殖,并通过复杂的信号通路加剧炎症反应,这也是 RA 的治疗靶点。因此,识别缺氧可能有助于评估 RA 疾病的活动性和定制治疗策略。为了探究多模态光声/超声成像能否帮助评估 RA 患者局部滑膜组织氧合状态,有研究纳入 118 例 RA 患者和 15 例健康志愿者,对 RA 患者进行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评估疾病活动度,并对 RA 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进行多模态光声/超声成像;根据测量滑膜所得的血氧饱和度值将 RA 患者进行分组,分析比较了组间能量多普勒半定量评分和疾病活动度间关联性及差异性;其结果显示低氧状态的关节滑膜虽可能具有较少的血管分布但与较高的疾病活动度相关[30]。因此,PAI 测定组织氧饱和度对 RA 的诊断评估具有补充价值,多模态光声/超声成像有望优化并提升传统超声对 RA 患者的评估并指导后续治疗。
最近,具有 PAI 效能的纳米材料在 RA 诊疗一体化中的应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Chen 等[31]构建了以仿生巨噬细胞膜为载体,同时包封普鲁士蓝和 TNF-α/IL-6 沉默 RNA 的纳米材料(M@P-siRNAsT/I),在该体系中,对 RA 小鼠模型进行治疗的同时还可通过近红外 PAI 实时、无创监测 M@P-siRNAsT/I 对 RA 微环境的靶向能力,并有效评估治疗效果。该研究成果为 PAI 技术辅助 RA 的诊断、治疗和监测提供了新策略[31]。此外,有研究设计了一个双模型分子成像体系;叶酸受体靶向的 Cptnc-4F 纳米探针具有第二近红外区强吸收和发射优势,能够通过光声断层成像将巨噬细胞在深层组织中的空间分布可视化,并提供巨噬细胞的精确位置和动态变化[32]。由于巨噬细胞在 RA 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巨噬细胞的多尺度可视化对 RA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证明了多功能纳米探针可用于监测 RA 小鼠模型巨噬细胞的变化,在 RA 的早期诊断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32]。
3 医工结合应用于 RA 治疗
3.1 纳米载体
由于传统治疗药物存在高剂量、频繁给药、缺乏特异性以及难以靶向病变关节等不足,因此开发纳米载体系统是目前提高治疗有效性的方法之一。纳米载体系统可以提高包封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靶向能力,通过缓释作用增加药物稳定性、防止生化降解,递送更多药物在滑膜关节的炎症微环境中积累。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索不同类型的纳米载体系统,主要包括基于脂质、聚合物以及生物囊泡的载体[33]。
3.1.1 脂质纳米载体
脂质纳米载体由磷脂作为主要成分,通常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几乎无毒、可降解且产物毒性低的特点,包括脂质体、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脂质体、醇质体和固体脂质纳米颗粒等[34]。
脂质体是一种囊泡状纳米载体,由含有卵磷脂和磷脂酰乙醇胺的磷脂双分子层组成,膜表面可通过修饰提高靶向的有效性,并且增加脂质体的循环时间降低网状内皮系统对脂质体的识别和清除。脂质体可以同时有效地传递亲水性和疏水性分子。亲水性药物通常在脂质体自组装过程中被动包封载入内部水相,而疏水性药物采用跨膜梯度方式封装和稳定在脂质体双分子层膜间[35]。有研究基于乙醇注射的原理开发了一种新的预浓缩方法准备脂质体;该脂质体具有较小的粒径和多分散指数,无需挤压工艺;结果显示甲氨蝶呤是通过氢键与主要磷脂相互作用提高了药物包封率;体内实验表明,包封甲氨蝶呤的脂质体在关节炎动物模型中显著增提高了抗炎疗效[36]。为了探究纳米载体负载药物同时治疗肿瘤和 RA 的作用,有研究制备了一种唾液酸修饰的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DOX-SAL),该脂质体可以在体内特异性靶向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并选用 S180 肉瘤细胞和胶原诱导 RA 共病的小鼠模型,结果显示 DOX-SAL 不仅可抑制肿瘤生长还能够减轻全身 RA 症状[37]。该研究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合并症的进展还改善了小鼠的生活质量,为 RA 合并症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创新的概念[37]。
3.1.2 聚合物纳米载体
由于脂质纳米载体存在稳定性差、清除快、生物分布低、对药物控释能力较差等不足,其研究与应用受到限制,而聚合物纳米载体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利用天然或合成聚合物作为选择性递送药物的载体系统具有延长系统半衰期、提高生物利用度、控制释放、免受 pH 值和酶降解影响等优势。同样通过表面配体修饰后,聚合物纳米载体能够与特定的炎性表达位点或受体结合从而表现出靶向性[38]。
最近,有研究设计了一种生物相容性和响应敏感的聚合物纳米载体用于治疗小鼠关节炎模型;他们以 N-(2-羟丙基)甲基丙烯酰胺基聚合物为载体,搭载抗炎药物地塞米松,通过调整纳米载体的流体动力学尺寸后,能够延长其在血液循环的时间,同时增强炎症部位的积累,将地塞米松释放后由肾脏代谢聚合物载体;与游离地塞米松不同,聚合物纳米载体在低剂量给药浓度下依然能够缓解关节炎以及骨质破坏[39]。目前,传统聚合物纳米载体中使用的聚合物大多是合成辅料或纯载体形式存在,不具有生物活性,难以实现多靶向或联合治疗。一些天然聚合物不仅能够作为载体,还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结合药物传递与治疗的作用进行疾病治疗。为此,有研究设计合成了一种治疗性透明质酸衍生物作为聚合物载体,实现青藤碱在炎性关节区域的控释;该聚合物载体具有软骨下骨吸附能力、能长时间在炎症关节内滞留并清除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ROS);其动物实验表明,与游离青藤碱注射剂相比,该聚合物载体可以增加关节润滑、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同时释放的药物下调炎性细胞因子[40]。这种药物结合治疗性聚合物的设计策略开辟了 RA 联合治疗的新领域。尽管如此,聚合物纳米载体发展仍然面临体内蓄积、粒子聚集、代谢产物毒性、开发周期长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进行大量临床试验。
3.1.3 胞外囊泡载体
尽管数十年来有大量关于纳米载体治疗疾病的研究,但由于安全性和低效靶向性使其难以在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近年来,胞外囊泡作为一种生物纳米载体,已成为实现疾病治疗的一种有希望的替代方案。胞外囊泡是几乎所有细胞类型都会分泌的磷脂双分子层封闭囊泡,载有多种蛋白质、mRNA 和 miRNA。根据大小和生物发生的不同,胞外囊泡主要分为外泌体(<150 nm)、微囊泡(150~
抗活性氧型胶原蛋白是一种针对关节炎受损软骨的抗体,有研究将该抗体与胞外囊泡结合,通过全身给药后表现出特异性靶向关节炎区域的能力,使复合物穿透软骨进入关节腔并仍保持抗体活性,表明了胞外囊泡具有成为药物靶向递送载体的潜力[46]。随后,利用胞外囊泡本身的主动靶向性,有研究用巨噬细胞分泌的胞外囊泡装载儿茶素类抗氧化药物研究其对 RA 的软骨修复作用;其结果发现胞外囊泡递送比单独给予儿茶素更有利于减少关节肿胀和滑膜增生,同时增加软骨Ⅱ型胶原的表达、减少软骨细胞的凋亡[47]。IL-4 能够促进巨噬细胞向 M2 型极化从而下调炎症,考虑到 IL-4 需要进入细胞腔才能作用,研究者通过基因工程开发了携带 IL-4 的胞外囊泡;与单独给予 IL-4 治疗对比,携带 IL-4 的胞外囊泡能够更好地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而表现出高抗炎作用,充分说明了胞外囊泡作为药物递送系统具有高效利用药物并放大其疗效的潜力[45]。然而,与上述其他载体相比,胞外囊泡载体目前因缺少高效分离技术而难以大量制备;此外,其药物负载技术尚不成熟;同时,具有高转移能力的细胞可以分泌胞外囊泡到低度恶性的细胞,导致肿瘤进展加速,进一步限制了其作为药物载体的大规模应用。
3.2 纳米酶
RA 关节中滑膜大量增生以及炎性细胞浸润,导致巨噬细胞向 M1 亚型大量分化,从而诱导大量 ROS 产生[48]。因此,调控 ROS 微环境也是目前广泛研究治疗 RA 的策略之一。虽然天然酶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和底物特异性,能够有效调控 ROS 而在工业、医学和生物领域被广泛研究,但其固有的缺陷如制备和纯化成本高、操作稳定性低、催化活性对环境条件敏感、回收和再利用困难等都限制了其应用。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者们设计了一系列具有酶催化活性的纳米材料,称之为纳米酶[49]。根据组成不同,相比天然酶,纳米酶在疾病治疗领域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针对 RA 的仿酶治疗也成为研究热点。
虽然类似硫代硫酸金钠等含金(Ⅰ)价态的化合物能够阻止 RA 的进展,但由于其高毒性和不良副作用限制其在临床应用。与金化合物相比,金属纳米团簇具有超小尺寸、高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固有的生物活性等优势。利用这一特性,有研究制备了纳米金团簇探究其在Ⅱ型胶原诱导的大鼠关节炎模型中的疗效和机制;其发现纳米金团簇能有效抑制炎症且无明显全身副作用;此外,纳米金团簇通过下调破骨细胞的表达从而直接抑制核因子-κB 配体,最终将软骨/骨的破坏逆转到正常状态[50]。除了金通过固有生物活性进行抗炎治疗,还有许多金属也可以相互协同来维持氧化还原平衡。有研究设计了铁锰纳米颗粒和铈纳米颗粒锚定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酶复合体,协同清除 ROS 并产生氧气,从而改善乏氧微环境以降低 M1 型巨噬细胞水平、诱导 M2 型巨噬细胞来治疗 RA。此外,该纳米酶复合体还可以用作药物递送载体,持续释放甲氨蝶呤增强治疗效果[51]。目前单一酶活性已不能满足纳米酶疾病治疗的需求,为了探索多酶体系,有研究构建了二维金属有机框架纳米酶;有机金属框架中的锌原子能够调节锰卟啉配位结构,使其同时模拟2种典型的抗氧化酶活性;细胞实验和体内动物模型都验证了该纳米酶独特的抗炎性能[52]。这些纳米酶研究拓宽了人们对纳米催化抗炎概念的了解,为今后 RA 抗炎治疗提供新想法。
3.3 水凝胶支架
水凝胶是亲水性聚合物之间通过交联反应形成的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可水膨胀聚合物材料,其具有良好的材料交换能力、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和可调节的力学性能。此外,水凝胶凭借其仿生特性,可以模拟细胞外基质的内部环境,促进细胞分化和组织生长。水凝胶主要包括天然水凝胶、合成水凝胶以及复合水凝胶。天然水凝胶在促进细胞黏附、迁移、分化和生长方面更有优势,但存在机械强度低、生物降解速率不可控和潜在的免疫原性反应等不足;而合成水凝胶具有结构可调节性、耐久性和机械强度高的特点,但缺乏生物活性[53-55]。近年来,随着医工交叉的发展,水凝胶在 RA 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RA 特殊的生理环境也对水凝胶的治疗提出了挑战。因此,各种研究对水凝胶进行改性以提高其应用的综合性能。
由于脂肪源性干细胞固有的抗炎和免疫调节特性,其可作为 RA 治疗的替代方法。为了解决直接注射干细胞出现存活率低和功能丧失的问题,有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细胞外基质激发的可注射水凝胶用于干细胞的包封和 RA 治疗;研究人员通过可逆的席夫碱交联反应构建了具有树突状聚赖氨酸和多糖组分的水凝胶;在拥有自愈能力和优异的力学性能的同时,其能够直接调控巨噬细胞表型并抑制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迁移进行抗炎治疗[56]。除了搭载干细胞,有研究将丝素蛋白水凝胶支架与干细胞衍生的外泌体进行原位光交联,达到对 RA 免疫微环境持久治疗的作用;该原位水凝胶体系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能够有效保护关节,同时外泌体通过抑制炎症通路从而有效地缓解滑膜炎症[57]。在RA 发生发展过程中,内源性一氧化氮因平衡被破坏而大量产生,因此清除一氧化氮也是治疗炎性疾病的另一种策略。有研究构建了一氧化氮响应的大尺寸水凝胶,其通过丙烯酰胺与一氧化氮可切割交联剂溶液聚合而得,当凝胶暴露在一氧化氮环境中时通过消耗一氧化氮分子来降低炎症水平[58]。除了可注射水凝胶,透皮水凝胶具有给药方便、良好的缓释及控释性能等特点,从而在皮肤组织发挥储留作用。有研究设计了 pH 响应的透皮水凝胶负载布洛芬纳米颗粒治疗 RA 小鼠;其结果表明,该水凝胶体系在急、慢性 RA 小鼠模型中均表现出治疗作用,证明了透皮水凝胶的应用前景[59]。
4 小结与展望
医工结合的出现,拓宽了人们对于 RA 诊疗的思路,使其不再局限于传统检测方法和药物的设计。随着医工结合概念的提出以及对 RA 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数十年的探索已经涌现大量的前沿研究,部分已应用于 RA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等临床领域中。尽管如此,由于疾病的复杂性、诊断技术的不稳定性以及纳米药物的合成和安全性等问题,医工结合在 RA 疾病诊疗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工作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因此,提高治疗效果的同时着重于生物安全性、精准靶向性和生物成像能力是未来 RA 诊疗研究的发展方向。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种常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全球发病率为 0.5%~1%,30~60 岁女性最常见[1]。RA 以对称性多关节疼痛和肿胀为主要特征,可累及全身多个大小关节,表现为滑膜增生、新生血管生成、进行性软骨损伤、骨侵蚀和关节畸形[2]。此外,RA 可引起关节外器官并发症,如贫血、肺间质性病变、心肌梗死、脑卒中等,最终导致严重的功能退化而致终身残疾,预期寿命明显降低,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3]。目前,RA 诊疗仍面临着重大挑战,迫切需要创新模式以提高早期诊断和高效治疗的能力。医工结合是多学科融合的领域,旨在通过工程技术的创新应用解决医学领域面临的挑战,包括生物医学检测、生物医学材料、医疗人工智能等多个新兴领域,有利于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4-5]。然而,该领域在 RA 诊断与治疗应用方面缺乏系统综述。因此,本文就近年来医工结合新技术在 RA 诊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以期拓展 RA 诊疗的新思路。
1 基于 RA 诊疗需求的医工结合
RA 发病机制错综复杂,存在遗传因素、环境暴露和免疫系统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涉及多种免疫细胞(如 T 细胞、B 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巨噬细胞等)以及非免疫细胞(如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等),它们在疾病持续进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7]。炎症反应是 RA 发病的核心,多种免疫细胞、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形成交织的正反馈通路。研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处于炎性细胞因子级联反应的顶端,驱动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1β和 IL-6 的表达。RA 骨免疫代谢同时受炎症因子和骨代谢效应细胞调控[8],炎症因子刺激下游滑膜细胞、破骨细胞等效应细胞导致滑膜组织过度增生从而破坏骨代谢动态平衡,是破坏关节的病理基础。此外,RA 滑膜组织呈“肿瘤样”过度增生时会诱导局部组织缺氧、血管通透性增加并刺激新生血管生成,同时,炎症微环境中存在高水平一氧化氮、活性氮及活性氧,其与炎症反应相互作用,导致细胞突变、遗传毒性和基因组大量缺失,促进疾病进展,最终在 RA 晚期刺激破骨细胞降解骨基质、溶解骨钙从而发生骨侵蚀[1, 3]。
由于 RA 是一种或多种共存条件以及关节外表现相关的全身性疾病,疾病呈连续的过程,起源于无症状的免疫功能障碍,并在关节症状之前经历不同阶段,因此其疾病机制也可能随着疾病的不同阶段而变化[2]。RA 早期滑膜成纤维细胞的表观遗传标记与疾病晚期的表观遗传标记有很大不同,抗瓜氨酸蛋白抗体(anti citrullinated protein antibodie, ACPA)的特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9]。因此,RA 诊疗策略强调在疾病早期进行更积极的干预[10]。
现有 RA 诊断方法主要通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与影像学评估相结合。2010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和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提出新的 RA 分类标准和评分系统,其中 ACPA、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s, RF)、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有助于 RA 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11]。其中,ACPA 是疾病早期发现的主要内源性抗体,对预测关节侵蚀具有更高价值,然而其虽然特异度较高,可达到 90%,灵敏度只有 50%~75%;RF 作为 RA 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其阳性率为 75%~80%,当呈高滴度阳性时可提示患者关节炎症状的严重程度,但还可见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或非感染性疾病;CRP 和 ESR 也可用于 RA 诊断,但均为非特异性炎症因子,主要用于评估机体疾病活动度[12]。RA 诊断的影像学技术包括 X 线、CT、MRI 和肌骨超声。X 线片和 CT 在评估关节结构损害具有优势,但软组织分辨率差,难以显示疾病初期滑膜炎等病变;MRI 和超声是评估早期关节炎最主要的成像技术,然而 MRI 特异性低且成本高昂从而限制临床应用,超声具有便捷、可重复性、无创性等优点,能够实时动态地诊断及监测疗效[13]。尽管影像学发展至今对 RA 诊断日趋成熟,但由于早期 RA 症状不明显,导致影像学技术仍然对其检出受限。因此,提高 RA 血清学标志物以及影像学技术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是早期诊断 RA 的关键。
目前 RA 的临床治疗目标包括改善病情、缓解关节肿痛并且抑制滑膜炎、防止疾病的发展、预防关节软骨损伤和骨侵蚀从而保护关节的整体功能,其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 GC)、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 DMARD)、生物制剂及靶向药物[14]。GC 能够快速减轻关节炎症状,被广泛应用于早期和活动期 RA,系统性使用 GC 能够达到改善病情的目的,延缓病情的发展,防止关节损伤;然而长期或者大剂量使用 GC 会加重感染风险,特别是对老年患者,其不良反应中骨质疏松和感染最常见。NSAID 具有良好的抗炎和解热镇痛作用,尽管它们广泛用于缓解症状,但不能减缓 RA 的病情发展,同时 NSAID 的使用也会产生肠胃不适、消化道溃疡、急性肾功能损伤以及心血管问题等不良反应。DMARD 作为治疗 RA 的一线用药,通常耐受性良好,其目的在于早期缓解关节炎症状,降低骨和软骨破坏,阻止疾病的发展[15-16]。根据 RA 的严重程度、患者的耐受程度和并发症,DMARD 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药物联用达到更好疗效。生物制剂近年来发展迅速,其主要通过阻断疾病过程中的关键炎症细胞因子或细胞表面分子而发挥治疗作用,如 TNF-α抑制剂、IL-6 抑制剂、IL-1 受体拮抗剂、T 细胞抑制剂和诱导 B 细胞凋亡单克隆抗体(CD20 单抗)等。上述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但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然需要改进,长期的药物使用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也体现在非靶器官、组织及细胞上,如胃肠道症状、免疫抑制、感染和新生肿瘤等。因此,寻找针对 RA 治疗的创新策略从而减少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医工结合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展现出良好的前景。医工结合将临床医学的迫切需求和先进的工程技术手段相融合,解决了许多临床医学的难点及痛点,不仅推动了新型医学诊疗技术的研发,还加速了智能医疗与健康管理的创新,从而提升了临床诊疗水平,并实现医疗服务的革命性提升。在 RA 诊断与治疗方面,医工结合也具有巨大潜力,例如利用微纳米技术开发生物传感器或结合纳米探针开发分子影像技术用于 RA 精准诊断,应用多模态新型成像技术定量评估 RA 活动度,设计纳米生物材料作为载体或仿生药物实现 RA 靶向分子水平治疗等。因此,医工结合的突破和创新有望改善基于传统 RA 诊疗的需求和不足。
2 医工结合应用于 RA 诊断
2.1 生物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是由生物敏感材料识别系统和理化换能器结合的分析工具,生物元件固定在固态表面上,与目标分析物进行特异性作用,最后将生化响应转换为可测量的输出信号[17]。生物传感器的开发实现了在单一平台上快速、特异性筛选生物标志物的可能,并提升了检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是帮助早期诊断疾病的重要工具,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新型生物传感器技术还可以利用高度个性化的诊断、便携化检测和实时监测改善 RA 患者的诊疗体验。目前,针对 RA 的生物传感器主要集中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和光学生物传感器[19-22]。
ACPA 和 RF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诊断 RA 的生物标志物。有研究设计一种能够同时测定 RF 和 ACPA 的简便、快速的双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其结果显示,该传感器对 RF 和 ACPA 均具有很高的灵敏度[23]。此外,该生物传感器还具有很强的选择性;2个靶标的定量检测可在 2 h 内同时完成,而所需样品体积仅需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的 1/4[23]。对比传统单独检测方法,该多重生物传感器具有更高的检测效率,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随后有研究利用各向异性有机-无机杂化纳米颗粒独特的光学特性制备了各向异性双金属聚合物纳米簇来作为光学免疫生物传感器;作为基于表面增强拉曼散射信号的纳米探针,其通过抗原-抗体相互作用定量分析 RF 和 ACPA 2 种 RA 生物标志物,证明了生物标志物浓度与拉曼强度之间的定量关系,且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在低浓度范围也可显示拉曼强度;由于快速和高灵敏度的检测能力,该新型多重光学生物传感器可替代商业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满足当前对 RA 早期诊断的需求[24]。
2.2 光声成像(photoacoustic imaging, PAI)
PAI 是一种混合成像技术,在可调节的电磁波长范围内发射激光并接收超声信号以形成图像,目标信号的强度与光吸收量成正比。PAI 结合了光学成像和超声成像的优势,同时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和深穿透度的特点,可以在多个波长下观察到人体内的固有物质,包括氧合和脱氧血红蛋白、黑色素、水、脂质等[25-26]。PAI 能够在可见光谱范围内定量氧化和脱氧血红蛋白,也可以测量血红蛋白的一些功能指标,同时实现形态和功能成像;此外,外源性光学纳米载体的出现使 PAI 在分子成像方面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及药物递送的监测。由于 PAI 的多功能成像特点,其作为一种创新的光学成像技术已被逐渐应用在实验动物和临床研究中,包括关节成像领域[27-29]。
组织缺氧会引发异常免疫细胞的激活和增殖,并通过复杂的信号通路加剧炎症反应,这也是 RA 的治疗靶点。因此,识别缺氧可能有助于评估 RA 疾病的活动性和定制治疗策略。为了探究多模态光声/超声成像能否帮助评估 RA 患者局部滑膜组织氧合状态,有研究纳入 118 例 RA 患者和 15 例健康志愿者,对 RA 患者进行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评估疾病活动度,并对 RA 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进行多模态光声/超声成像;根据测量滑膜所得的血氧饱和度值将 RA 患者进行分组,分析比较了组间能量多普勒半定量评分和疾病活动度间关联性及差异性;其结果显示低氧状态的关节滑膜虽可能具有较少的血管分布但与较高的疾病活动度相关[30]。因此,PAI 测定组织氧饱和度对 RA 的诊断评估具有补充价值,多模态光声/超声成像有望优化并提升传统超声对 RA 患者的评估并指导后续治疗。
最近,具有 PAI 效能的纳米材料在 RA 诊疗一体化中的应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Chen 等[31]构建了以仿生巨噬细胞膜为载体,同时包封普鲁士蓝和 TNF-α/IL-6 沉默 RNA 的纳米材料(M@P-siRNAsT/I),在该体系中,对 RA 小鼠模型进行治疗的同时还可通过近红外 PAI 实时、无创监测 M@P-siRNAsT/I 对 RA 微环境的靶向能力,并有效评估治疗效果。该研究成果为 PAI 技术辅助 RA 的诊断、治疗和监测提供了新策略[31]。此外,有研究设计了一个双模型分子成像体系;叶酸受体靶向的 Cptnc-4F 纳米探针具有第二近红外区强吸收和发射优势,能够通过光声断层成像将巨噬细胞在深层组织中的空间分布可视化,并提供巨噬细胞的精确位置和动态变化[32]。由于巨噬细胞在 RA 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巨噬细胞的多尺度可视化对 RA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证明了多功能纳米探针可用于监测 RA 小鼠模型巨噬细胞的变化,在 RA 的早期诊断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32]。
3 医工结合应用于 RA 治疗
3.1 纳米载体
由于传统治疗药物存在高剂量、频繁给药、缺乏特异性以及难以靶向病变关节等不足,因此开发纳米载体系统是目前提高治疗有效性的方法之一。纳米载体系统可以提高包封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靶向能力,通过缓释作用增加药物稳定性、防止生化降解,递送更多药物在滑膜关节的炎症微环境中积累。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索不同类型的纳米载体系统,主要包括基于脂质、聚合物以及生物囊泡的载体[33]。
3.1.1 脂质纳米载体
脂质纳米载体由磷脂作为主要成分,通常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几乎无毒、可降解且产物毒性低的特点,包括脂质体、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脂质体、醇质体和固体脂质纳米颗粒等[34]。
脂质体是一种囊泡状纳米载体,由含有卵磷脂和磷脂酰乙醇胺的磷脂双分子层组成,膜表面可通过修饰提高靶向的有效性,并且增加脂质体的循环时间降低网状内皮系统对脂质体的识别和清除。脂质体可以同时有效地传递亲水性和疏水性分子。亲水性药物通常在脂质体自组装过程中被动包封载入内部水相,而疏水性药物采用跨膜梯度方式封装和稳定在脂质体双分子层膜间[35]。有研究基于乙醇注射的原理开发了一种新的预浓缩方法准备脂质体;该脂质体具有较小的粒径和多分散指数,无需挤压工艺;结果显示甲氨蝶呤是通过氢键与主要磷脂相互作用提高了药物包封率;体内实验表明,包封甲氨蝶呤的脂质体在关节炎动物模型中显著增提高了抗炎疗效[36]。为了探究纳米载体负载药物同时治疗肿瘤和 RA 的作用,有研究制备了一种唾液酸修饰的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DOX-SAL),该脂质体可以在体内特异性靶向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并选用 S180 肉瘤细胞和胶原诱导 RA 共病的小鼠模型,结果显示 DOX-SAL 不仅可抑制肿瘤生长还能够减轻全身 RA 症状[37]。该研究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合并症的进展还改善了小鼠的生活质量,为 RA 合并症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创新的概念[37]。
3.1.2 聚合物纳米载体
由于脂质纳米载体存在稳定性差、清除快、生物分布低、对药物控释能力较差等不足,其研究与应用受到限制,而聚合物纳米载体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利用天然或合成聚合物作为选择性递送药物的载体系统具有延长系统半衰期、提高生物利用度、控制释放、免受 pH 值和酶降解影响等优势。同样通过表面配体修饰后,聚合物纳米载体能够与特定的炎性表达位点或受体结合从而表现出靶向性[38]。
最近,有研究设计了一种生物相容性和响应敏感的聚合物纳米载体用于治疗小鼠关节炎模型;他们以 N-(2-羟丙基)甲基丙烯酰胺基聚合物为载体,搭载抗炎药物地塞米松,通过调整纳米载体的流体动力学尺寸后,能够延长其在血液循环的时间,同时增强炎症部位的积累,将地塞米松释放后由肾脏代谢聚合物载体;与游离地塞米松不同,聚合物纳米载体在低剂量给药浓度下依然能够缓解关节炎以及骨质破坏[39]。目前,传统聚合物纳米载体中使用的聚合物大多是合成辅料或纯载体形式存在,不具有生物活性,难以实现多靶向或联合治疗。一些天然聚合物不仅能够作为载体,还具有抗氧化作用,能够结合药物传递与治疗的作用进行疾病治疗。为此,有研究设计合成了一种治疗性透明质酸衍生物作为聚合物载体,实现青藤碱在炎性关节区域的控释;该聚合物载体具有软骨下骨吸附能力、能长时间在炎症关节内滞留并清除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ROS);其动物实验表明,与游离青藤碱注射剂相比,该聚合物载体可以增加关节润滑、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同时释放的药物下调炎性细胞因子[40]。这种药物结合治疗性聚合物的设计策略开辟了 RA 联合治疗的新领域。尽管如此,聚合物纳米载体发展仍然面临体内蓄积、粒子聚集、代谢产物毒性、开发周期长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进行大量临床试验。
3.1.3 胞外囊泡载体
尽管数十年来有大量关于纳米载体治疗疾病的研究,但由于安全性和低效靶向性使其难以在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近年来,胞外囊泡作为一种生物纳米载体,已成为实现疾病治疗的一种有希望的替代方案。胞外囊泡是几乎所有细胞类型都会分泌的磷脂双分子层封闭囊泡,载有多种蛋白质、mRNA 和 miRNA。根据大小和生物发生的不同,胞外囊泡主要分为外泌体(<150 nm)、微囊泡(150~
抗活性氧型胶原蛋白是一种针对关节炎受损软骨的抗体,有研究将该抗体与胞外囊泡结合,通过全身给药后表现出特异性靶向关节炎区域的能力,使复合物穿透软骨进入关节腔并仍保持抗体活性,表明了胞外囊泡具有成为药物靶向递送载体的潜力[46]。随后,利用胞外囊泡本身的主动靶向性,有研究用巨噬细胞分泌的胞外囊泡装载儿茶素类抗氧化药物研究其对 RA 的软骨修复作用;其结果发现胞外囊泡递送比单独给予儿茶素更有利于减少关节肿胀和滑膜增生,同时增加软骨Ⅱ型胶原的表达、减少软骨细胞的凋亡[47]。IL-4 能够促进巨噬细胞向 M2 型极化从而下调炎症,考虑到 IL-4 需要进入细胞腔才能作用,研究者通过基因工程开发了携带 IL-4 的胞外囊泡;与单独给予 IL-4 治疗对比,携带 IL-4 的胞外囊泡能够更好地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而表现出高抗炎作用,充分说明了胞外囊泡作为药物递送系统具有高效利用药物并放大其疗效的潜力[45]。然而,与上述其他载体相比,胞外囊泡载体目前因缺少高效分离技术而难以大量制备;此外,其药物负载技术尚不成熟;同时,具有高转移能力的细胞可以分泌胞外囊泡到低度恶性的细胞,导致肿瘤进展加速,进一步限制了其作为药物载体的大规模应用。
3.2 纳米酶
RA 关节中滑膜大量增生以及炎性细胞浸润,导致巨噬细胞向 M1 亚型大量分化,从而诱导大量 ROS 产生[48]。因此,调控 ROS 微环境也是目前广泛研究治疗 RA 的策略之一。虽然天然酶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和底物特异性,能够有效调控 ROS 而在工业、医学和生物领域被广泛研究,但其固有的缺陷如制备和纯化成本高、操作稳定性低、催化活性对环境条件敏感、回收和再利用困难等都限制了其应用。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研究者们设计了一系列具有酶催化活性的纳米材料,称之为纳米酶[49]。根据组成不同,相比天然酶,纳米酶在疾病治疗领域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针对 RA 的仿酶治疗也成为研究热点。
虽然类似硫代硫酸金钠等含金(Ⅰ)价态的化合物能够阻止 RA 的进展,但由于其高毒性和不良副作用限制其在临床应用。与金化合物相比,金属纳米团簇具有超小尺寸、高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固有的生物活性等优势。利用这一特性,有研究制备了纳米金团簇探究其在Ⅱ型胶原诱导的大鼠关节炎模型中的疗效和机制;其发现纳米金团簇能有效抑制炎症且无明显全身副作用;此外,纳米金团簇通过下调破骨细胞的表达从而直接抑制核因子-κB 配体,最终将软骨/骨的破坏逆转到正常状态[50]。除了金通过固有生物活性进行抗炎治疗,还有许多金属也可以相互协同来维持氧化还原平衡。有研究设计了铁锰纳米颗粒和铈纳米颗粒锚定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酶复合体,协同清除 ROS 并产生氧气,从而改善乏氧微环境以降低 M1 型巨噬细胞水平、诱导 M2 型巨噬细胞来治疗 RA。此外,该纳米酶复合体还可以用作药物递送载体,持续释放甲氨蝶呤增强治疗效果[51]。目前单一酶活性已不能满足纳米酶疾病治疗的需求,为了探索多酶体系,有研究构建了二维金属有机框架纳米酶;有机金属框架中的锌原子能够调节锰卟啉配位结构,使其同时模拟2种典型的抗氧化酶活性;细胞实验和体内动物模型都验证了该纳米酶独特的抗炎性能[52]。这些纳米酶研究拓宽了人们对纳米催化抗炎概念的了解,为今后 RA 抗炎治疗提供新想法。
3.3 水凝胶支架
水凝胶是亲水性聚合物之间通过交联反应形成的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可水膨胀聚合物材料,其具有良好的材料交换能力、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和可调节的力学性能。此外,水凝胶凭借其仿生特性,可以模拟细胞外基质的内部环境,促进细胞分化和组织生长。水凝胶主要包括天然水凝胶、合成水凝胶以及复合水凝胶。天然水凝胶在促进细胞黏附、迁移、分化和生长方面更有优势,但存在机械强度低、生物降解速率不可控和潜在的免疫原性反应等不足;而合成水凝胶具有结构可调节性、耐久性和机械强度高的特点,但缺乏生物活性[53-55]。近年来,随着医工交叉的发展,水凝胶在 RA 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RA 特殊的生理环境也对水凝胶的治疗提出了挑战。因此,各种研究对水凝胶进行改性以提高其应用的综合性能。
由于脂肪源性干细胞固有的抗炎和免疫调节特性,其可作为 RA 治疗的替代方法。为了解决直接注射干细胞出现存活率低和功能丧失的问题,有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型细胞外基质激发的可注射水凝胶用于干细胞的包封和 RA 治疗;研究人员通过可逆的席夫碱交联反应构建了具有树突状聚赖氨酸和多糖组分的水凝胶;在拥有自愈能力和优异的力学性能的同时,其能够直接调控巨噬细胞表型并抑制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迁移进行抗炎治疗[56]。除了搭载干细胞,有研究将丝素蛋白水凝胶支架与干细胞衍生的外泌体进行原位光交联,达到对 RA 免疫微环境持久治疗的作用;该原位水凝胶体系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能够有效保护关节,同时外泌体通过抑制炎症通路从而有效地缓解滑膜炎症[57]。在RA 发生发展过程中,内源性一氧化氮因平衡被破坏而大量产生,因此清除一氧化氮也是治疗炎性疾病的另一种策略。有研究构建了一氧化氮响应的大尺寸水凝胶,其通过丙烯酰胺与一氧化氮可切割交联剂溶液聚合而得,当凝胶暴露在一氧化氮环境中时通过消耗一氧化氮分子来降低炎症水平[58]。除了可注射水凝胶,透皮水凝胶具有给药方便、良好的缓释及控释性能等特点,从而在皮肤组织发挥储留作用。有研究设计了 pH 响应的透皮水凝胶负载布洛芬纳米颗粒治疗 RA 小鼠;其结果表明,该水凝胶体系在急、慢性 RA 小鼠模型中均表现出治疗作用,证明了透皮水凝胶的应用前景[59]。
4 小结与展望
医工结合的出现,拓宽了人们对于 RA 诊疗的思路,使其不再局限于传统检测方法和药物的设计。随着医工结合概念的提出以及对 RA 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数十年的探索已经涌现大量的前沿研究,部分已应用于 RA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等临床领域中。尽管如此,由于疾病的复杂性、诊断技术的不稳定性以及纳米药物的合成和安全性等问题,医工结合在 RA 疾病诊疗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工作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因此,提高治疗效果的同时着重于生物安全性、精准靶向性和生物成像能力是未来 RA 诊疗研究的发展方向。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