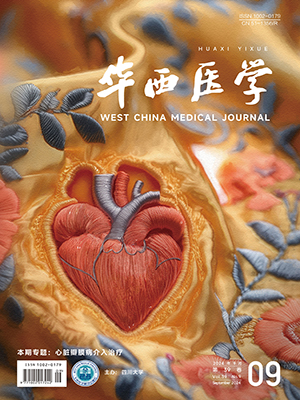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是临床推进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促进患者身心康复的重要举措。但目前针对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缺乏可靠证据推荐指导临床护理实践。为此,中华护理学会骨科护理专业委员会、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四川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以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为主题,根据循证医学证据,结合相关领域专家临床经验,形成专家共识,提出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 9 条推荐意见,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引用本文: 中华护理学会骨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 四川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 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护理专家共识. 华西医学, 2024, 39(10): 1514-1519. doi: 10.7507/1002-0179.202406247 复制
颈椎前路手术是一种从颈椎前侧入路行颈椎病治疗的骨科手术术式,可用于治疗颈椎骨折、颈椎肿瘤、颈椎退行性变等颈椎疾病[1]。颈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颈前路椎体次全切除融合术及颈前路混合减压融合术是临床常见颈椎前路手术方案,无论何种手术方案,其目的均为去除或减轻血管、神经根或脊髓的受压症状,提高颈椎稳定性[1-2]。颈椎前路术式具有微创、稳定性高等优势,但该入路术式因手术切口较深,术区与食道、气管、颈动脉鞘和前颈肌肉等复杂组织结构相邻,患者术后易发生因喉头水肿、引流不充分、疼痛导致的呼吸道、胃肠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3-4]。研究证实,早期下床活动是保障颈椎前路术后充分引流、镇痛、促进患者呼吸与胃肠等功能恢复的重要举措[5]。但是,目前针对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亦无相关指南及共识发布。本共识基于最新循证证据及专家实践经验,形成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方案,旨在为临床医生、护士和相关专业人员提供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决策依据,规范临床医疗和护理行为。
1 共识制订
1.1 共识制订成员
本共识由 14 名共识撰写成员、10 名共识撰写指导专家(5 名骨科护理专家、3 名骨科医疗专家、1 名心理学专家及 1 名循证医学专家)和 47 名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函询骨科护理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共识专家遴选标准:① 从事骨科护理和/或医疗、心理卫生、循证医学相关领域工作≥10 年;② 本科及以上学历;③ 副高及以上职称;④ 自愿参与本课题。
成员任务分工:撰写成员负责检索、分析文献,组织专家就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实施过程关键点、临床护理难点进行论证,收集专家意见,通过整理、分析专家意见,形成本共识初稿,再根据护理专家函询反馈结果,对共识内容进行修订;共识撰写指导专家负责在共识制订过程中对共识内容进行指导和质量控制;共识函询专家主要负责对共识内容进行评价与审核。
1.2 共识主题和主要内容修订
共识撰写成员通过查阅文献、组织指导专家讨论,确定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相关关键问题。根据主题与关键问题,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结合的检索形式,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Clinical Evidence 数据库,限定检索文献语种为中文或英文,检索时间范围为数据库建库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撰写成员及指导专家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完成文献证据筛选,提取质量较高的证据[6-8],编写共识的基本内容。
1.3 专家函询,形成终稿
共识撰写组采用电子邮件发放和组织线上会议的形式进行了 2 轮专家咨询以及专家论证。撰写组对收集的专家意见进行梳理,并查找文献予以论证,达成一致后对共识内容进行修改,根据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文献证据等级划分标准确定共识内容推荐强度[9]。进一步采用德尔菲法对共识每条推荐证据进行反复评估,收集专家“赞同”“反对”“不确定”的反馈意见,根据“赞同”专家数所占百分比,得出专家共识度,最后形成共识终稿内容。
2 共识内容
2.1 背景概述
2.1.1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定义
关于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标准。2019 年《颈椎前路手术加速康复外科实施流程专家共识》指出,患者术后麻醉清醒后 2 h 即可下床[10],完成术后早期离床活动。近年来,有研究将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定义为患者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在术后 24~72 h[11]。鉴于颈椎前路手术患者的个性特点,为保障下床活动安全性,患者应在身心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术后尽早离床进行活动,以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术后康复。
2.1.2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意义
相关研究证实,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颈椎前路手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12-13]。同样,术后早期下床活动能够促进身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肌肉力量、肺功能、胃肠功能等),减轻术后疼痛,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达到快速康复的目的,缩短住院时间[14]。另外,在多学科协作基础上开展的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方案,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间专业知识的互相交流融合,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的相关理论及前沿知识。
2.2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风险评估
全面、准确的评估是科学开展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前提,应及早筛查阻碍患者下床活动的风险因素,以便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帮助患者早期下床活动。
2.2.1 意识与生命体征
推荐意见 1: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征稳定在正常范围是安全下床活动的前提。患者下床活动前,医务人员应充分评估患者意识、配合程度,实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在患者清醒、配合、生命体征平稳时协助其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100%)。
颈椎前路手术患者一般接受全身麻醉配合手术治疗。全身麻醉通过吸入和/静脉注射麻醉药物,使患者出现可逆性意识丧失、痛觉消失和肌肉松弛,确保手术顺利进行。手术结束后,如患者受麻醉残余药物影响未完全复苏,可出现意识障碍、定向障碍等临床症状,严重者甚至出现躁动及心理异常,如盲目下床活动可造成跌倒、坠床等严重后果。因此,为确保患者安全,术后下床活动前,评判患者麻醉复苏情况及配合度至关重要。当患者完全清醒,呼吸频率恢复正常,可自主完成深呼吸、咳嗽,血压恢复至术前±20% 以内,呼吸空气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92% 后协助患者做下床准备,必要时可借用麻醉复苏评估量表进行测评,协助判定患者意识及生命体征恢复情况[15]。
2.2.2 营养状况
推荐意见 2:患者营养状况可直接影响其下床活动能力,营养风险患者应给予营养支持治疗,以确保患者术后下床活动安全。正确使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动态评估患者术后营养风险,配合医生、营养师及照护者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营养支持方案,患者营养支持目标血清白蛋白>35 g/L(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93%)。
患者营养状态与其活动能力密切相关。当患者营养成分摄入不足时,机体分解代谢增加,肌肉含量减少,肌力受损,下床活动过程中跌倒、活动不耐受等风险增高。活动前对患者营养状况的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干预营养不良,保障患者安全。可采用营养风险筛查 2002 量表或微型营养评估量表筛查患者营养风险,对于营养不良高风险患者及早介入营养干预[16]。对于存在严重营养风险的患者,如营养风险筛查 2002 量表评分>5 分、血清白蛋白<30 g/L 者[17-18],应避免盲目的下床活动训练,以免造成患者活动不耐受、跌倒甚至晕厥。应在医护、营养师及康复治疗师的共同评定下,制定适合患者的营养支持方案和个性化活动方案[19]。
2.2.3 运动功能
推荐意见 3:术后直立不耐受患者应谨慎下床活动,下床活动前可使用徒手肌力测试等方法评估患者肌力水平,当患者下肢徒手肌力测试≥3 级时,可协助其下床活动(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95%)。
颈椎前路术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前,进行直立不耐受风险和肌力水平等运动功能评估是保证患者活动安全的重要措施。当患者由卧位变换为直立位时,如果出现头晕、大汗、恶心等脑供血不足表现,或直立后 3 min 内出现收缩压下降 20 mm Hg(1 mm Hg=0.133 kPa)以上、舒张压下降 10 mm Hg 以上的异常情况,提示患者可能存在直立不耐受,应谨慎下床活动[20-21]。临床可采用徒手肌力测试患者肌力水平,徒手肌力评估分级法:0 级表示没有肌肉收缩;1 级表示有肌肉收缩,但无主动肢体活动;2 级表示可完成肢体主动活动,但不抗重力;3 级表示抗重力但不抗阻力完成主动活动;4 级表示可抗重力和部分阻力完成主动活动;5 级表示可完成抗重力和阻力的主动活动。当患者下肢肌力在 3 级及以上、循环稳定的情况下可协助患者下床,进行步行康复锻炼[22-23]。
2.2.4 心理状态
推荐意见 4:住院环境、手术、围手术期治疗干预均可能成为患者负性心理状态的应激源,医务人员应在患者围手术期全程动态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及早识别患者负性情绪,必要时使用心理测评工具、邀请心理学专业人员协同干预,避免患者负性心理状态影响术后早期下床活动依从性(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研究表明,术后抑郁、焦虑的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更差,且首次下床活动的时间相对延长[24]。医务人员可通过量表测评和主观评估法评估患者心理状态。量表测评可使用患者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等工具完成。主观评估法可通过观察、交谈等方式评估患者的表情、主诉内容及行为是否与量表测评结果相符[22],从而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异常心理状态。此外,还要警惕患者是否存在因疼痛困扰造成的恐动症。恐动症是对运动极端恐惧的一种心理表现,指患者因受到疼痛性伤害或损伤造成的疼痛敏感性增强,对身体活动产生的一种过度的、非理性恐惧[25]。可运用恐动症 Tampa 量表等测量患者的恐动程度,对恐动患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多学科康复训练等改善恐动症状,恢复日常活动[26]。
2.2.5 管路安全
推荐意见 5:对于颈椎前路手术术后带管患者,医务人员应关注管道固定、引流、引流口周围皮肤及患者全身症状等情况,病情允许情况下尽早拔除各类留置管道,提高患者下床活动安全性及舒适度;对于术后因治疗需要,确需留置管道且医生评估可带管下床活动者,应保证管道稳妥固定,必要时使用移动输液架、移动置物架等器具辅助患者下床活动(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100%)。
术后如留置切口引流管、尿管、静脉输液通路、吸氧管路、安置心电监护导联线等可能限制患者下床活动,带管活动也存在跌倒、非计划管道脱落等潜在风险。管路安全评估是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前的必备工作,需评估引流管路固定是否稳妥、引流是否通畅、引流液颜色性状是否正常等。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应尽早拔除管道,以促进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27]。因病情需要留置管道的患者,必要时可使用移动输液架、移动置物架等器具辅助下床活动,保障下床活动安全性。如患者术后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切口引流管引流淡红色或淡黄色清亮液体明显增多,应警惕术后脑脊液漏并发症,此时不可下床活动,应协助患者平卧,以减轻脑脊液漏导致的低颅压症状[28-29]。
2.3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实施措施
2.3.1 健康宣教
推荐意见 6: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开展前后,应向患者、家属及其他照护者进行有效的知识宣教及正向反馈,以宣教对象能接纳的形式讲解下床活动相关知识与注意事项,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早期下床活动方案中(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患者对早期下床活动的相关知识掌握水平会直接影响其健康行为。因此,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在术后早期下床活动中十分重要。① 宣教对象:包括患者、家属及照护者,作为早期下床活动的主体和辅助者均应掌握早期下床活动的流程及注意事项。② 宣教方式:根据患者文化背景和意愿,采用多模式宣教,如知识讲座、面对面交流、书面指导或视频影像宣教等。③ 宣教内容:向患者及其家属行一对一的康复指导,解释医务人员采取各项操作的原因,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及配合,鼓励患者积极参与下床活动;告知下床活动的必要性、具体方法、活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2.3.2 镇痛管理
推荐意见 7:关注患者疼痛主诉,正确使用疼痛评估工具反馈患者疼痛,采用物理、心理及药物治疗等多模式镇痛方案,促进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100%)。
围手术期镇痛管理是缓解患者疼痛的关键,应关注患者主诉,动态评估患者疼痛,及时干预,缓解患者疼痛,提高患者舒适度及下床活动依从性。疼痛评估工具,如数字疼痛评估(Numerical Rating Scale)、视觉模拟疼痛评估(Visual Analogue Scale)评估简便,易被患者接纳[30-31]。根据患者个体情况,使用镇痛药物、骨骼肌松弛剂等药物,缓解伤口疼痛、神经根性疼痛。同时,还可使用心理学认知行为干预技术,如正念冥想、音乐疗法等帮助患者缓解疼痛[32-33]。尽量减少阿片类镇痛药物的使用,避免随之而来的恶心、呕吐、尿潴留、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34]。
2.3.3 下床活动训练
推荐意见 8:医生、康复治疗师及护士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和需求,形成包括下床活动方式、下床活动时长及下床活动频率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密切关注下床运动过程中患者安全,促进康复训练目标达成(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① 下床活动方式:协助患者由卧位到坐位,再到床边站立位、离床行走训练过渡。首先保持坐位,适应 30 s 以上,若无不适,再协助患者床旁站立或踮脚,适应 30 s 以上,若无不适再进行步行训练。若患者不耐受下床活动,可在床上行功能锻炼及床周边活动。② 下床活动时长:以患者自身情况而定,在其能耐受的范围内,10~20 min/次,每日可适当逐渐增加行走时长。③ 下床活动的频率: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首次下床时,在活动耐受情况下,建议至少步行距离 5 m,每天步行 2 次;之后视患者耐受情况逐渐增加活动强度[35-36]。活动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身心状况,可使用便携式指脉氧仪监测患者活动过程中的心率及氧饱和度,一旦患者有心慌、头晕、乏力或氧饱和度<90% 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活动,协助患者卧床休息并采取吸氧、补液等相应的处理措施[36]。
2.4 效果评价
推荐意见 9:早期下床活动方案实施后,医务人员应采用量化指标评价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实施效果,同时注重患者自我报告结局结果,为更新、改进早期下床活动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医务人员可通过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活动功能、住院时长、住院费用等指标评价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实施效果。除医务人员主导的下床活动后效果评价外,不可忽视患者自我报告结局在临床的重要价值,如疼痛评估、满意度评价、生活质量评价等。此外,还可使用核心结果衡量指数(Core Outcome Measure Index)等对颈椎前路术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效果进行针对性评价[37]。
3 结语
本研究基于循证证据及国内专家临床实践经验,就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早期下床活动的评估、早期下床活动的内容等方面,形成了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方案专家共识,可为临床医务人员提供参考证据。目前,国内的研究在关于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具体实施内容方面仍较为模糊,后续仍有较大的细化空间。随着加速康复的广泛推广与应用,未来还需纳入更多全面、科学的研究以完善证据的细节内容,以期为临床提供适用的循证证据。
共识执笔:张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雨慧(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雅磊(北京协和医院),王立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朱红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佩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尹子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忠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杨辉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佳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宁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亚萍(北京协和医院),孟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修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指导专家(排名不分先后):杜春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冯乐玲(宁波市第六医院),高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黄雪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玲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宋跃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贝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曾建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共识专家(排名不分先后):包春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陈佳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晶(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陈琳(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陈亚萍(北京协和医院),房玉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付红英(贵州省人民医院),高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郭锦丽(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韩云(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胡靖(西安市红会医院),胡三莲(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黄洁(北京积水潭医院),黄天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伦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秀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李叶萍(绵阳市中心医院),李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翠青(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艳(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龙彩雪(海南省人民医院),鲁建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鲁雪梅(北京积水潭医院),罗春梅(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闵燕(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彭伶丽(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裴艳玲(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史凌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史晓娟(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宋国敏(天津市天津医院),苏晓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薛慧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谭晓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唐永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田昕(陕西省人民医院),王洁(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琦(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明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吴松梅(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熊健(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许蕊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杨银玲(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瑛(宁波市第六医院),张秀芳(深圳市中医院),周文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利益冲突:执笔作者和专家组成员均无相关利益冲突。
免责声明:本共识仅供临床医护人员参考应用,不作为任何医疗纠纷及诉讼的法律依据。
颈椎前路手术是一种从颈椎前侧入路行颈椎病治疗的骨科手术术式,可用于治疗颈椎骨折、颈椎肿瘤、颈椎退行性变等颈椎疾病[1]。颈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颈前路椎体次全切除融合术及颈前路混合减压融合术是临床常见颈椎前路手术方案,无论何种手术方案,其目的均为去除或减轻血管、神经根或脊髓的受压症状,提高颈椎稳定性[1-2]。颈椎前路术式具有微创、稳定性高等优势,但该入路术式因手术切口较深,术区与食道、气管、颈动脉鞘和前颈肌肉等复杂组织结构相邻,患者术后易发生因喉头水肿、引流不充分、疼痛导致的呼吸道、胃肠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3-4]。研究证实,早期下床活动是保障颈椎前路术后充分引流、镇痛、促进患者呼吸与胃肠等功能恢复的重要举措[5]。但是,目前针对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亦无相关指南及共识发布。本共识基于最新循证证据及专家实践经验,形成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方案,旨在为临床医生、护士和相关专业人员提供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决策依据,规范临床医疗和护理行为。
1 共识制订
1.1 共识制订成员
本共识由 14 名共识撰写成员、10 名共识撰写指导专家(5 名骨科护理专家、3 名骨科医疗专家、1 名心理学专家及 1 名循证医学专家)和 47 名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函询骨科护理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共识专家遴选标准:① 从事骨科护理和/或医疗、心理卫生、循证医学相关领域工作≥10 年;② 本科及以上学历;③ 副高及以上职称;④ 自愿参与本课题。
成员任务分工:撰写成员负责检索、分析文献,组织专家就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实施过程关键点、临床护理难点进行论证,收集专家意见,通过整理、分析专家意见,形成本共识初稿,再根据护理专家函询反馈结果,对共识内容进行修订;共识撰写指导专家负责在共识制订过程中对共识内容进行指导和质量控制;共识函询专家主要负责对共识内容进行评价与审核。
1.2 共识主题和主要内容修订
共识撰写成员通过查阅文献、组织指导专家讨论,确定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相关关键问题。根据主题与关键问题,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结合的检索形式,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Clinical Evidence 数据库,限定检索文献语种为中文或英文,检索时间范围为数据库建库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撰写成员及指导专家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完成文献证据筛选,提取质量较高的证据[6-8],编写共识的基本内容。
1.3 专家函询,形成终稿
共识撰写组采用电子邮件发放和组织线上会议的形式进行了 2 轮专家咨询以及专家论证。撰写组对收集的专家意见进行梳理,并查找文献予以论证,达成一致后对共识内容进行修改,根据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文献证据等级划分标准确定共识内容推荐强度[9]。进一步采用德尔菲法对共识每条推荐证据进行反复评估,收集专家“赞同”“反对”“不确定”的反馈意见,根据“赞同”专家数所占百分比,得出专家共识度,最后形成共识终稿内容。
2 共识内容
2.1 背景概述
2.1.1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定义
关于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标准。2019 年《颈椎前路手术加速康复外科实施流程专家共识》指出,患者术后麻醉清醒后 2 h 即可下床[10],完成术后早期离床活动。近年来,有研究将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定义为患者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在术后 24~72 h[11]。鉴于颈椎前路手术患者的个性特点,为保障下床活动安全性,患者应在身心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术后尽早离床进行活动,以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术后康复。
2.1.2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意义
相关研究证实,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颈椎前路手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12-13]。同样,术后早期下床活动能够促进身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肌肉力量、肺功能、胃肠功能等),减轻术后疼痛,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达到快速康复的目的,缩短住院时间[14]。另外,在多学科协作基础上开展的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方案,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间专业知识的互相交流融合,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的相关理论及前沿知识。
2.2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风险评估
全面、准确的评估是科学开展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前提,应及早筛查阻碍患者下床活动的风险因素,以便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帮助患者早期下床活动。
2.2.1 意识与生命体征
推荐意见 1: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征稳定在正常范围是安全下床活动的前提。患者下床活动前,医务人员应充分评估患者意识、配合程度,实时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在患者清醒、配合、生命体征平稳时协助其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100%)。
颈椎前路手术患者一般接受全身麻醉配合手术治疗。全身麻醉通过吸入和/静脉注射麻醉药物,使患者出现可逆性意识丧失、痛觉消失和肌肉松弛,确保手术顺利进行。手术结束后,如患者受麻醉残余药物影响未完全复苏,可出现意识障碍、定向障碍等临床症状,严重者甚至出现躁动及心理异常,如盲目下床活动可造成跌倒、坠床等严重后果。因此,为确保患者安全,术后下床活动前,评判患者麻醉复苏情况及配合度至关重要。当患者完全清醒,呼吸频率恢复正常,可自主完成深呼吸、咳嗽,血压恢复至术前±20% 以内,呼吸空气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92% 后协助患者做下床准备,必要时可借用麻醉复苏评估量表进行测评,协助判定患者意识及生命体征恢复情况[15]。
2.2.2 营养状况
推荐意见 2:患者营养状况可直接影响其下床活动能力,营养风险患者应给予营养支持治疗,以确保患者术后下床活动安全。正确使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动态评估患者术后营养风险,配合医生、营养师及照护者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营养支持方案,患者营养支持目标血清白蛋白>35 g/L(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93%)。
患者营养状态与其活动能力密切相关。当患者营养成分摄入不足时,机体分解代谢增加,肌肉含量减少,肌力受损,下床活动过程中跌倒、活动不耐受等风险增高。活动前对患者营养状况的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干预营养不良,保障患者安全。可采用营养风险筛查 2002 量表或微型营养评估量表筛查患者营养风险,对于营养不良高风险患者及早介入营养干预[16]。对于存在严重营养风险的患者,如营养风险筛查 2002 量表评分>5 分、血清白蛋白<30 g/L 者[17-18],应避免盲目的下床活动训练,以免造成患者活动不耐受、跌倒甚至晕厥。应在医护、营养师及康复治疗师的共同评定下,制定适合患者的营养支持方案和个性化活动方案[19]。
2.2.3 运动功能
推荐意见 3:术后直立不耐受患者应谨慎下床活动,下床活动前可使用徒手肌力测试等方法评估患者肌力水平,当患者下肢徒手肌力测试≥3 级时,可协助其下床活动(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95%)。
颈椎前路术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前,进行直立不耐受风险和肌力水平等运动功能评估是保证患者活动安全的重要措施。当患者由卧位变换为直立位时,如果出现头晕、大汗、恶心等脑供血不足表现,或直立后 3 min 内出现收缩压下降 20 mm Hg(1 mm Hg=0.133 kPa)以上、舒张压下降 10 mm Hg 以上的异常情况,提示患者可能存在直立不耐受,应谨慎下床活动[20-21]。临床可采用徒手肌力测试患者肌力水平,徒手肌力评估分级法:0 级表示没有肌肉收缩;1 级表示有肌肉收缩,但无主动肢体活动;2 级表示可完成肢体主动活动,但不抗重力;3 级表示抗重力但不抗阻力完成主动活动;4 级表示可抗重力和部分阻力完成主动活动;5 级表示可完成抗重力和阻力的主动活动。当患者下肢肌力在 3 级及以上、循环稳定的情况下可协助患者下床,进行步行康复锻炼[22-23]。
2.2.4 心理状态
推荐意见 4:住院环境、手术、围手术期治疗干预均可能成为患者负性心理状态的应激源,医务人员应在患者围手术期全程动态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及早识别患者负性情绪,必要时使用心理测评工具、邀请心理学专业人员协同干预,避免患者负性心理状态影响术后早期下床活动依从性(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研究表明,术后抑郁、焦虑的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更差,且首次下床活动的时间相对延长[24]。医务人员可通过量表测评和主观评估法评估患者心理状态。量表测评可使用患者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等工具完成。主观评估法可通过观察、交谈等方式评估患者的表情、主诉内容及行为是否与量表测评结果相符[22],从而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异常心理状态。此外,还要警惕患者是否存在因疼痛困扰造成的恐动症。恐动症是对运动极端恐惧的一种心理表现,指患者因受到疼痛性伤害或损伤造成的疼痛敏感性增强,对身体活动产生的一种过度的、非理性恐惧[25]。可运用恐动症 Tampa 量表等测量患者的恐动程度,对恐动患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多学科康复训练等改善恐动症状,恢复日常活动[26]。
2.2.5 管路安全
推荐意见 5:对于颈椎前路手术术后带管患者,医务人员应关注管道固定、引流、引流口周围皮肤及患者全身症状等情况,病情允许情况下尽早拔除各类留置管道,提高患者下床活动安全性及舒适度;对于术后因治疗需要,确需留置管道且医生评估可带管下床活动者,应保证管道稳妥固定,必要时使用移动输液架、移动置物架等器具辅助患者下床活动(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100%)。
术后如留置切口引流管、尿管、静脉输液通路、吸氧管路、安置心电监护导联线等可能限制患者下床活动,带管活动也存在跌倒、非计划管道脱落等潜在风险。管路安全评估是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前的必备工作,需评估引流管路固定是否稳妥、引流是否通畅、引流液颜色性状是否正常等。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应尽早拔除管道,以促进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27]。因病情需要留置管道的患者,必要时可使用移动输液架、移动置物架等器具辅助下床活动,保障下床活动安全性。如患者术后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切口引流管引流淡红色或淡黄色清亮液体明显增多,应警惕术后脑脊液漏并发症,此时不可下床活动,应协助患者平卧,以减轻脑脊液漏导致的低颅压症状[28-29]。
2.3 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实施措施
2.3.1 健康宣教
推荐意见 6: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开展前后,应向患者、家属及其他照护者进行有效的知识宣教及正向反馈,以宣教对象能接纳的形式讲解下床活动相关知识与注意事项,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早期下床活动方案中(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患者对早期下床活动的相关知识掌握水平会直接影响其健康行为。因此,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在术后早期下床活动中十分重要。① 宣教对象:包括患者、家属及照护者,作为早期下床活动的主体和辅助者均应掌握早期下床活动的流程及注意事项。② 宣教方式:根据患者文化背景和意愿,采用多模式宣教,如知识讲座、面对面交流、书面指导或视频影像宣教等。③ 宣教内容:向患者及其家属行一对一的康复指导,解释医务人员采取各项操作的原因,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及配合,鼓励患者积极参与下床活动;告知下床活动的必要性、具体方法、活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2.3.2 镇痛管理
推荐意见 7:关注患者疼痛主诉,正确使用疼痛评估工具反馈患者疼痛,采用物理、心理及药物治疗等多模式镇痛方案,促进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推荐强度:A 级;共识度:100%)。
围手术期镇痛管理是缓解患者疼痛的关键,应关注患者主诉,动态评估患者疼痛,及时干预,缓解患者疼痛,提高患者舒适度及下床活动依从性。疼痛评估工具,如数字疼痛评估(Numerical Rating Scale)、视觉模拟疼痛评估(Visual Analogue Scale)评估简便,易被患者接纳[30-31]。根据患者个体情况,使用镇痛药物、骨骼肌松弛剂等药物,缓解伤口疼痛、神经根性疼痛。同时,还可使用心理学认知行为干预技术,如正念冥想、音乐疗法等帮助患者缓解疼痛[32-33]。尽量减少阿片类镇痛药物的使用,避免随之而来的恶心、呕吐、尿潴留、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34]。
2.3.3 下床活动训练
推荐意见 8:医生、康复治疗师及护士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和需求,形成包括下床活动方式、下床活动时长及下床活动频率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密切关注下床运动过程中患者安全,促进康复训练目标达成(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① 下床活动方式:协助患者由卧位到坐位,再到床边站立位、离床行走训练过渡。首先保持坐位,适应 30 s 以上,若无不适,再协助患者床旁站立或踮脚,适应 30 s 以上,若无不适再进行步行训练。若患者不耐受下床活动,可在床上行功能锻炼及床周边活动。② 下床活动时长:以患者自身情况而定,在其能耐受的范围内,10~20 min/次,每日可适当逐渐增加行走时长。③ 下床活动的频率: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首次下床时,在活动耐受情况下,建议至少步行距离 5 m,每天步行 2 次;之后视患者耐受情况逐渐增加活动强度[35-36]。活动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的身心状况,可使用便携式指脉氧仪监测患者活动过程中的心率及氧饱和度,一旦患者有心慌、头晕、乏力或氧饱和度<90% 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活动,协助患者卧床休息并采取吸氧、补液等相应的处理措施[36]。
2.4 效果评价
推荐意见 9:早期下床活动方案实施后,医务人员应采用量化指标评价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实施效果,同时注重患者自我报告结局结果,为更新、改进早期下床活动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推荐强度:B 级;共识度:100%)。
医务人员可通过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活动功能、住院时长、住院费用等指标评价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实施效果。除医务人员主导的下床活动后效果评价外,不可忽视患者自我报告结局在临床的重要价值,如疼痛评估、满意度评价、生活质量评价等。此外,还可使用核心结果衡量指数(Core Outcome Measure Index)等对颈椎前路术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效果进行针对性评价[37]。
3 结语
本研究基于循证证据及国内专家临床实践经验,就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早期下床活动的评估、早期下床活动的内容等方面,形成了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方案专家共识,可为临床医务人员提供参考证据。目前,国内的研究在关于颈椎前路手术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具体实施内容方面仍较为模糊,后续仍有较大的细化空间。随着加速康复的广泛推广与应用,未来还需纳入更多全面、科学的研究以完善证据的细节内容,以期为临床提供适用的循证证据。
共识执笔:张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雨慧(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雅磊(北京协和医院),王立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朱红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佩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尹子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忠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杨辉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佳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宁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亚萍(北京协和医院),孟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修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指导专家(排名不分先后):杜春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冯乐玲(宁波市第六医院),高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黄雪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玲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宋跃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贝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曾建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共识专家(排名不分先后):包春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陈佳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晶(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陈琳(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陈亚萍(北京协和医院),房玉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付红英(贵州省人民医院),高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郭锦丽(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韩云(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胡靖(西安市红会医院),胡三莲(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黄洁(北京积水潭医院),黄天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伦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秀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李叶萍(绵阳市中心医院),李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翠青(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艳(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龙彩雪(海南省人民医院),鲁建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鲁雪梅(北京积水潭医院),罗春梅(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闵燕(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彭伶丽(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裴艳玲(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史凌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史晓娟(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宋国敏(天津市天津医院),苏晓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薛慧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谭晓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唐永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田昕(陕西省人民医院),王洁(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琦(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明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吴松梅(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熊健(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许蕊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杨银玲(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瑛(宁波市第六医院),张秀芳(深圳市中医院),周文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利益冲突:执笔作者和专家组成员均无相关利益冲突。
免责声明:本共识仅供临床医护人员参考应用,不作为任何医疗纠纷及诉讼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