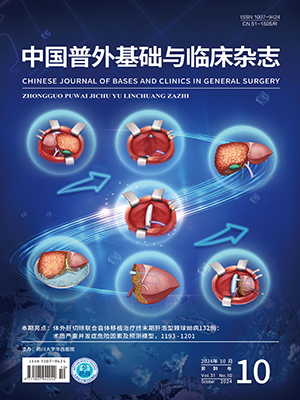引用本文: 李川, 王川, 张晓赟, 文天夫. 肝动脉结扎对梗阻性黄疸大鼠残肝肝细胞凋亡及再生的影响.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7, 24(1): 24-31. doi: 10.7507/1007-9424.201609056 复制
胆管癌是第二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大约占消化系统肿瘤的3%[1]。近年来,胆管癌的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据报道[2],美国每年新增约3 000例胆管癌患者,50%~60%为肝门胆管癌。肝门胆管癌的早期诊断较困难。由于肝门部解剖结构较复杂,肝门胆管癌诊断时常有门静脉和(或)肝动脉侵犯,其根治性切除率较低。尽管有研究[3-4]认为,肝门胆管癌伴门静脉或肝动脉侵犯时,同时行门静脉或肝动脉切除重建能够提高患者生存率,但有时肝门部血管重建较困难,尤其是肝动脉。既往笔者的临床研究[5]中发现,对伴有肝动脉侵犯的肝门胆管癌患者,同时行左半肝联合肝固有动脉切除可以提高切除率,且并不增加患者围手术期风险。但肝固有动脉切除后对剩余肝脏肝细胞的凋亡及再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拟通过大鼠梗阻性黄疸模型,研究肝切除联合肝动脉结扎对剩余肝脏肝细胞凋亡及再生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1.1.1 实验动物 8 周龄Wistar雄性大鼠80只,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科技园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质量240~260 g。大鼠进入动物饲养房,分笼后常规喂养 1 周,以适应动物房环境;实验前动物称重,体质量为(282±24)g。
1.1.2 实验动物分组 实验动物分为 4 组,每组大鼠20只。即:建立梗阻性黄疸模型后 3 d施行70%肝切除+肝固有动脉结扎+胆肠内引流组(A组);建立梗阻性黄疸模型后 3 d施行70%肝切除+胆肠内引流(B组);假手术后 3 d施行70%肝切除+肝固有动脉结扎(C组)和假手术后 3 d施行70%肝切除(D组)。
1.2 主要仪器、试剂
① 日立7170A型自动生化检测仪(Hitach,Japan);② TUNEL罗氏免疫荧光原位凋亡检测试剂盒(Roche,Swiss);③ Brdu(Sigma,USA)
1.3 大鼠梗阻性黄疸模型建立方法
术前大鼠均禁食12 h、不禁饮,术后均立即给予自配10%葡萄糖水及常规饲料喂养。梗阻性黄疸模型建立方法:乙醚吸入麻醉后,大鼠仰卧位固定于手术台,腹部手术范围剃毛备皮后,用70%医用乙醇消毒 3 遍,铺无菌洞巾,自大鼠剑突向下作约1.5 cm长腹部正中切口;湿棉签辅助轻柔暴露肝十二指肠韧带,游离胆总管,距肝门处肝脏面1.2~1.5 cm处使用 1 号丝线近远端分别双重结扎胆总管,然后离断以防止再通,关腹、保温复苏。
各组大鼠于第 1 步手术后 3 d进行第 2 次手术。① 70%肝切除:采用Higgins等[6]的经典肝蒂结扎法切除大鼠左外叶(约30%)和中叶(约40%)。② 肝固有动脉结扎法:使用湿棉签将肝十二指肠韧带向左侧拨开后找到腹主动脉,在膈角处腹主动脉腹侧发出腹腔干,沿着腹腔干走行识别出肝总动脉,顺着肝总动脉走行识别出胃十二指肠动脉和肝固有动脉,游离出肝固有动脉,用 1 号丝线近远端分别双重结扎并离断。③ 胆肠内引流法:使用外径0.96 mm、长 2 cm外表给予磨砂和两端刻线处理(有利于丝线固定导管和组织)的硬膜外导管作为再通扩张的胆总管与十二指肠的通道,一端置入扩张的胆总管内,带线结扎固定,另一端置入幽门下方约 2 cm的十二指肠内,导管周围使用 1 号丝线荷包缝合固定,拉拢导管两端已固定的丝线再次打结固定,使扩张的胆总管与十二指肠紧密贴合防止漏胆。最后,检查腹腔无明显出血、漏胆后关腹,入笼保温复苏。术前、术中及术后 6 h内死亡的大鼠视为手术不当引起的死亡,不计入实验范畴的手术后死亡。对于每组大鼠术后的数量不足,给予同中心、同品系及同龄的大鼠补充,保证每组 4 个时间点上各有 5 只大鼠可取标本。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取材时间 4 组大鼠均在第 2 次70%切肝手术后的 1 d、2 d、3 d和 6 d 4 个时间点上通过心脏采血各处死 5 只,采集血液标本并切取肝脏标本备检。各组大鼠均在处死前 1 h,腹腔注射浓度为30 μg/L的Brdu溶液 1 mL。① 大鼠每次术前称重及术后每个时间点取标本前称重。② 记录每组大鼠的术后死亡数并分析死亡原因。③ 各组大鼠取血后 1 h内,室温下,3 000 r/min离心10 min(r=3 cm),取上层血清,–80 ℃保存备用。④ 各组大鼠心脏采血处死后,残肝取右外叶置入10%中性甲醛液中固定,24~48 h后石蜡包埋;另取三角叶立即放入液氮中保存,24 h后转入–80 ℃深低温冰箱保存备检。
1.4.2 检测指标 ① 血清标本采用日立7170A型自动生化检测仪测定血清胆红素(TB)、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白蛋白(ALB)水平。② 肝脏标本在10%中性甲醛液中固定24~48 h后,常规石蜡包埋,连续 4 μm厚切片,所有标本均行HE染色。③ 所有石蜡切片均行TUNEL法检测肝细胞凋亡情况。④ 所有石蜡切片均行Brdu细胞增殖标记的免疫组化染色,按ABC法进行检测,苏木精或伊红衬染。
1.4.3 结果判定标准 TUNEL阳性计数在荧光显微镜×400倍视野下计数发绿色荧光的阳性细胞数,以阳性细胞数除以细胞总数计算出肝脏组织细胞的凋亡指数(AI),每个标本计数 5 个视野,取其平均值,以百分数表示。Brdu定量细胞增殖结果判定:Brdu标记的细胞质及细胞核呈棕色则为Brdu标记阳性细胞。在显微镜下随机计数10个×400倍视野中的细胞总数及Brdu标记阳性细胞数,计算标记指数(RI,Brdu标记阳性细胞数/细胞总数),该指数即为肝细胞增殖指数。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χ2 检验或Fisher’s精确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术中情况及实验大鼠术后死亡情况及分析
梗阻性黄疸模型术后第 3 天,术中见大鼠腹腔中度可分离的粘连,腹腔脏器黄染;大鼠胆总管扩张明显,直径1.5~2 mm,胆管壁变薄呈透明状;肝脏肿胀明显,棕黄色,表面呈颗粒状表现。
实验共用114只 8 周龄Wistar雄性大鼠,4 组实验因第 1 次手术麻醉过深或手术不当共死亡 5 只。A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4 只,本实验术后6~24 h内死亡 9 只,手术成功率为87.9%(29/33),术后成活率为69.0%(20/29)。B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3 只,本实验术后6~24 h内死亡 8 只,手术成功率为90.3%(28/31),术后成活率为71.4%(20/28)。C 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2 只,手术成功率为90.9%(20/22),术后成活率为100%(20/20)。D 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3 只,手术成功率为87.0%(20/23),术后成活率为100%(20/20)。其中 A、B 2 组大鼠术后成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2),C、D 2 组大鼠术后成活率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1.000),但 A、B 2 组大鼠术后成活率均明显低于 C、D 2 组(P<0.05)。所有第 2 次术后6~24 h内死亡的动物均行尸检证实为非失血或漏胆引起的死亡,其死亡可能为肝功能衰竭所致。死亡大鼠即时用同中心、同品系的同龄大鼠予以补充。
2.2 各组大鼠肝功能指标检测结果
4 组大鼠术后不同时相血清TB、ALT、AST和ALB检测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A组和B组大鼠术后各时相肝功能的大多数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早期的ALB水平,A组低于B组(术后 3 d,P<0.05);C组和D组术后各时相肝功能指标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早期C组的ALB水平低于D组(术后 1 d和 3 d 均P<0.05)。
术后早期(术后 3 d 内)A、B 2 组大鼠的肝功能指标总体上要差于C、D 组(P<0.05);但在术后晚期(术后 6 d时)A、B 2 组大鼠的肝功能指标明显恢复,尤其是ALT和AST,与 C、D 组比较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血清TB水平,A、B 组仍明显高于C、D组(均P<0.05)。在肝脏淤胆状态下完成的A、B 2 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各时相的血清TB水平均明显高于肝脏正常状态下行70%肝切除的C、D 2 组(均P<0.05)。A、B 2 组大鼠术后其血清TB水平下降明显(术后 1 d比术后 6 d,P<0.05),提示胆肠内引流对梗阻性黄疸的引流效果明显。C、D 2 组大鼠肝切除术后 2 d和 3 d血清TB水平有所升高并达到高峰,这可能是肝脏切除和结扎肝动脉引起的肝脏损害造成的,之后则好转恢复。
2.3 肝脏组织的病理学改变
光镜下见:A组肝脏的肝索较清楚连贯,汇管区出现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肝细胞肿胀明显,细胞质广泛空泡化;B组肝脏的肝索清楚,汇管区同A组、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肝细胞肿胀,空泡化较多;C组和D组的肝脏其表现大体相似,肝索、汇管区清晰,无炎症细胞浸润,肝细胞形态较正常,无明显肿胀。具体见图 1。
 图1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残肝的的病理学改变(HE ×100) a:A组;b:B组;c:C组;d:D组
图1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残肝的的病理学改变(HE ×100) a:A组;b:B组;c:C组;d:D组
2.4 肝细胞凋亡指数检测结果
结果见图 2 及图 3。由图 2 和图 3 可见,TUNEL染色的蓝色背景下发绿色荧光的细胞为阳性凋亡肝细胞。A、B、C 3 个组术后 1 d残肝细胞凋亡指数达到最大,而后逐渐下降;与其他 3 组比较,D组残肝细胞凋亡指数在术后各时相均为最低;如图 4 所示,术后 1 d和 2 d 4 组大鼠的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凋亡指数为 A 组>B 组>C 组>D组;术后 3 d及 6 d,除C组与D组之间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各组两两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2
示TUNEL法检测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凋亡荧光图(TUNEL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发绿色荧光者为阳性凋亡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图2
示TUNEL法检测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凋亡荧光图(TUNEL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发绿色荧光者为阳性凋亡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图3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各时相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和 2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A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B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3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各时相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和 2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A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B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4
示Brdu标记的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增殖情况(Brdu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呈棕染的细胞为阳性增殖肝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图4
示Brdu标记的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增殖情况(Brdu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呈棕染的细胞为阳性增殖肝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2.5 肝细胞增殖指数检测结果
结果见图 4 和图 5。由图 4 和图 5 可见,Brdu增殖标记染色的细胞质或细胞核棕染的肝细胞为增殖肝细胞。在术后 1 d,C、D 2 组大鼠的肝细胞增殖达峰值,增殖指数大小为D组>C组>B组>A组,各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后 2 d,A、B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才达峰值,但 2 组间肝细胞增殖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仍明显高于A、B组,C组又明显高于其他 3 组,即A组比C组、A组比D组、B组比C组、B 组比D组和C组比D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除了C、D 2 组间肝细胞增殖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组两两间比较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6 d,A、B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无明显升高,C、D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明显降低,4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图5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不同时相残肝肝细胞增殖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2 d,C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5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不同时相残肝肝细胞增殖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2 d,C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目前,根治性切除是肝门胆管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但由于肝门部解剖结构复杂,且肝门胆管癌极易侵犯肝门部动脉和门静脉,使得肝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较困难。尽管血管切除重建并非手术禁止,但肝门胆管癌手术时有时血管重建仍较困难,尤其是肝动脉重建[4,7-8]。若对于这部分患者,行肝动脉切除后不予以重建势必可以增加患者根治性切除的机会。但对于肝门胆管癌患者肝动脉切除后不重建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Neuhaus等[9]分析了80例行肝切除的肝门胆管癌患者资料后指出,行门静脉切除者 5 年生存率可高达65%,明显高于未行门静脉切除的28%。但de Jong等[10]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指出,虽然联合肝切除与门静脉切除可提高肝门胆管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但其早期死亡风险明显高于未行门静脉切除者。
肝脏由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供血。常规情况下,肝总动脉自腹腔干发出后,主要分出肝固有动脉和胃十二指肠动脉,肝固有动脉又依次分出胃右动脉、肝左/右动脉和胆囊动脉。肝左右动脉分支入肝后,在肝门区或肝内延着Glisson鞘多次分支并伴随门静脉和肝管分支一起走行于Glisson鞘内,形成非常丰富的动脉侧支吻合。肝脏除了常规的肝动脉供应动脉血外,在肝周韧带内还存在多条侧支循环。当肝动脉被慢性侵犯或压闭阻塞时,肝脏侧支循环就会增粗变大,供血量明显增加。Michels等[11-13]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多次研究报告了肝脏的侧支循环。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14-16]亦证实,术前若肿瘤侵犯导致肝脏动脉血供完全阻断,并不会对肝脏功能产生巨大影响。笔者此前的研究[5]亦认为,对于术中拟切除肝动脉不予重建的患者,不要游离剩余肝脏的肝周韧带,以便保存侧支循环。本研究亦证实,肝动脉结扎后将增加肝细胞凋亡,减弱肝细胞再生能力。
细胞凋亡是由特定基因控制,在酶促反应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发生的细胞主动死亡过程,是机体维持自我平衡的一种生理机制[17]。在肝细胞凋亡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正常肝脏,行70%大部肝切除后大鼠或结扎肝动脉联合肝切除的大鼠来说,70%肝切除未明显促进残肝肝细胞凋亡,但是肝动脉的结扎明显促进了术后早期(2 d内)的肝细胞凋亡;而到了晚期(3 d后),2 组大鼠残肝肝细胞的凋亡情况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脏再生是残肝肝细胞通过有丝分裂形成新的细胞,恢复原来肝细胞数量和肝体积的生理机制。有研究[18]报道,大鼠大部肝切除术后,残肝肝细胞的DNA合成在24 h内达到高峰,7~10 d残肝即再生恢复到原来的肝脏体积。研究[18]发现,肝再生主要是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刺激内皮细胞形成新生血管并刺激肝细胞增殖完成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肝再生方面,正常肝脏状态下,70%肝切除或结扎肝动脉联合70%肝切除的大鼠都会在术后 2 d内达到增殖高峰;结扎肝动脉在切除术后早期(2 d内)减弱了大部肝切除大鼠的肝脏再生能力,但同时也延长了残肝肝细胞增殖的时间;在术后 6 d时,2 组的肝脏再生已接近完成。
多数学者[19-21]认为,梗阻性黄疸状态下,肝细胞凋亡是梗阻性黄疸引起肝细胞死亡并导致肝脏损害的主要原因,所以,肝脏功能的衰竭主要是由肝细胞的凋亡引起的。肝细胞凋亡在梗阻性黄疸的肝脏病理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梗阻性黄疸过程中,高浓度的胆汁酸盐直接损害肝细胞、引起肝细胞凋亡,再加上淤胆状态下机体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和大量细胞因子的产生,加剧了肝细胞的凋亡[22-24]。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梗阻性黄疸模型大鼠实施70%肝切除联合肝动脉结扎组较70%肝切除组肝细胞凋亡增加,再生能力减弱。但 2 组的术后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同时还发现,最影响肝细胞凋亡与肝脏再生的因素是梗阻性黄疸。
综上,本研究结果证实,结扎肝动脉将增加残肝肝细胞凋亡,减弱肝细胞再生。但结扎肝动脉并未增加梗阻性黄疸大鼠术后死亡风险。
胆管癌是第二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大约占消化系统肿瘤的3%[1]。近年来,胆管癌的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据报道[2],美国每年新增约3 000例胆管癌患者,50%~60%为肝门胆管癌。肝门胆管癌的早期诊断较困难。由于肝门部解剖结构较复杂,肝门胆管癌诊断时常有门静脉和(或)肝动脉侵犯,其根治性切除率较低。尽管有研究[3-4]认为,肝门胆管癌伴门静脉或肝动脉侵犯时,同时行门静脉或肝动脉切除重建能够提高患者生存率,但有时肝门部血管重建较困难,尤其是肝动脉。既往笔者的临床研究[5]中发现,对伴有肝动脉侵犯的肝门胆管癌患者,同时行左半肝联合肝固有动脉切除可以提高切除率,且并不增加患者围手术期风险。但肝固有动脉切除后对剩余肝脏肝细胞的凋亡及再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拟通过大鼠梗阻性黄疸模型,研究肝切除联合肝动脉结扎对剩余肝脏肝细胞凋亡及再生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1.1.1 实验动物 8 周龄Wistar雄性大鼠80只,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科技园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质量240~260 g。大鼠进入动物饲养房,分笼后常规喂养 1 周,以适应动物房环境;实验前动物称重,体质量为(282±24)g。
1.1.2 实验动物分组 实验动物分为 4 组,每组大鼠20只。即:建立梗阻性黄疸模型后 3 d施行70%肝切除+肝固有动脉结扎+胆肠内引流组(A组);建立梗阻性黄疸模型后 3 d施行70%肝切除+胆肠内引流(B组);假手术后 3 d施行70%肝切除+肝固有动脉结扎(C组)和假手术后 3 d施行70%肝切除(D组)。
1.2 主要仪器、试剂
① 日立7170A型自动生化检测仪(Hitach,Japan);② TUNEL罗氏免疫荧光原位凋亡检测试剂盒(Roche,Swiss);③ Brdu(Sigma,USA)
1.3 大鼠梗阻性黄疸模型建立方法
术前大鼠均禁食12 h、不禁饮,术后均立即给予自配10%葡萄糖水及常规饲料喂养。梗阻性黄疸模型建立方法:乙醚吸入麻醉后,大鼠仰卧位固定于手术台,腹部手术范围剃毛备皮后,用70%医用乙醇消毒 3 遍,铺无菌洞巾,自大鼠剑突向下作约1.5 cm长腹部正中切口;湿棉签辅助轻柔暴露肝十二指肠韧带,游离胆总管,距肝门处肝脏面1.2~1.5 cm处使用 1 号丝线近远端分别双重结扎胆总管,然后离断以防止再通,关腹、保温复苏。
各组大鼠于第 1 步手术后 3 d进行第 2 次手术。① 70%肝切除:采用Higgins等[6]的经典肝蒂结扎法切除大鼠左外叶(约30%)和中叶(约40%)。② 肝固有动脉结扎法:使用湿棉签将肝十二指肠韧带向左侧拨开后找到腹主动脉,在膈角处腹主动脉腹侧发出腹腔干,沿着腹腔干走行识别出肝总动脉,顺着肝总动脉走行识别出胃十二指肠动脉和肝固有动脉,游离出肝固有动脉,用 1 号丝线近远端分别双重结扎并离断。③ 胆肠内引流法:使用外径0.96 mm、长 2 cm外表给予磨砂和两端刻线处理(有利于丝线固定导管和组织)的硬膜外导管作为再通扩张的胆总管与十二指肠的通道,一端置入扩张的胆总管内,带线结扎固定,另一端置入幽门下方约 2 cm的十二指肠内,导管周围使用 1 号丝线荷包缝合固定,拉拢导管两端已固定的丝线再次打结固定,使扩张的胆总管与十二指肠紧密贴合防止漏胆。最后,检查腹腔无明显出血、漏胆后关腹,入笼保温复苏。术前、术中及术后 6 h内死亡的大鼠视为手术不当引起的死亡,不计入实验范畴的手术后死亡。对于每组大鼠术后的数量不足,给予同中心、同品系及同龄的大鼠补充,保证每组 4 个时间点上各有 5 只大鼠可取标本。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取材时间 4 组大鼠均在第 2 次70%切肝手术后的 1 d、2 d、3 d和 6 d 4 个时间点上通过心脏采血各处死 5 只,采集血液标本并切取肝脏标本备检。各组大鼠均在处死前 1 h,腹腔注射浓度为30 μg/L的Brdu溶液 1 mL。① 大鼠每次术前称重及术后每个时间点取标本前称重。② 记录每组大鼠的术后死亡数并分析死亡原因。③ 各组大鼠取血后 1 h内,室温下,3 000 r/min离心10 min(r=3 cm),取上层血清,–80 ℃保存备用。④ 各组大鼠心脏采血处死后,残肝取右外叶置入10%中性甲醛液中固定,24~48 h后石蜡包埋;另取三角叶立即放入液氮中保存,24 h后转入–80 ℃深低温冰箱保存备检。
1.4.2 检测指标 ① 血清标本采用日立7170A型自动生化检测仪测定血清胆红素(TB)、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白蛋白(ALB)水平。② 肝脏标本在10%中性甲醛液中固定24~48 h后,常规石蜡包埋,连续 4 μm厚切片,所有标本均行HE染色。③ 所有石蜡切片均行TUNEL法检测肝细胞凋亡情况。④ 所有石蜡切片均行Brdu细胞增殖标记的免疫组化染色,按ABC法进行检测,苏木精或伊红衬染。
1.4.3 结果判定标准 TUNEL阳性计数在荧光显微镜×400倍视野下计数发绿色荧光的阳性细胞数,以阳性细胞数除以细胞总数计算出肝脏组织细胞的凋亡指数(AI),每个标本计数 5 个视野,取其平均值,以百分数表示。Brdu定量细胞增殖结果判定:Brdu标记的细胞质及细胞核呈棕色则为Brdu标记阳性细胞。在显微镜下随机计数10个×400倍视野中的细胞总数及Brdu标记阳性细胞数,计算标记指数(RI,Brdu标记阳性细胞数/细胞总数),该指数即为肝细胞增殖指数。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χ2 检验或Fisher’s精确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术中情况及实验大鼠术后死亡情况及分析
梗阻性黄疸模型术后第 3 天,术中见大鼠腹腔中度可分离的粘连,腹腔脏器黄染;大鼠胆总管扩张明显,直径1.5~2 mm,胆管壁变薄呈透明状;肝脏肿胀明显,棕黄色,表面呈颗粒状表现。
实验共用114只 8 周龄Wistar雄性大鼠,4 组实验因第 1 次手术麻醉过深或手术不当共死亡 5 只。A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4 只,本实验术后6~24 h内死亡 9 只,手术成功率为87.9%(29/33),术后成活率为69.0%(20/29)。B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3 只,本实验术后6~24 h内死亡 8 只,手术成功率为90.3%(28/31),术后成活率为71.4%(20/28)。C 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2 只,手术成功率为90.9%(20/22),术后成活率为100%(20/20)。D 组第 2 次手术因麻醉过深或失血过多死亡 3 只,手术成功率为87.0%(20/23),术后成活率为100%(20/20)。其中 A、B 2 组大鼠术后成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2),C、D 2 组大鼠术后成活率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1.000),但 A、B 2 组大鼠术后成活率均明显低于 C、D 2 组(P<0.05)。所有第 2 次术后6~24 h内死亡的动物均行尸检证实为非失血或漏胆引起的死亡,其死亡可能为肝功能衰竭所致。死亡大鼠即时用同中心、同品系的同龄大鼠予以补充。
2.2 各组大鼠肝功能指标检测结果
4 组大鼠术后不同时相血清TB、ALT、AST和ALB检测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A组和B组大鼠术后各时相肝功能的大多数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早期的ALB水平,A组低于B组(术后 3 d,P<0.05);C组和D组术后各时相肝功能指标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早期C组的ALB水平低于D组(术后 1 d和 3 d 均P<0.05)。
术后早期(术后 3 d 内)A、B 2 组大鼠的肝功能指标总体上要差于C、D 组(P<0.05);但在术后晚期(术后 6 d时)A、B 2 组大鼠的肝功能指标明显恢复,尤其是ALT和AST,与 C、D 组比较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血清TB水平,A、B 组仍明显高于C、D组(均P<0.05)。在肝脏淤胆状态下完成的A、B 2 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各时相的血清TB水平均明显高于肝脏正常状态下行70%肝切除的C、D 2 组(均P<0.05)。A、B 2 组大鼠术后其血清TB水平下降明显(术后 1 d比术后 6 d,P<0.05),提示胆肠内引流对梗阻性黄疸的引流效果明显。C、D 2 组大鼠肝切除术后 2 d和 3 d血清TB水平有所升高并达到高峰,这可能是肝脏切除和结扎肝动脉引起的肝脏损害造成的,之后则好转恢复。
2.3 肝脏组织的病理学改变
光镜下见:A组肝脏的肝索较清楚连贯,汇管区出现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肝细胞肿胀明显,细胞质广泛空泡化;B组肝脏的肝索清楚,汇管区同A组、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肝细胞肿胀,空泡化较多;C组和D组的肝脏其表现大体相似,肝索、汇管区清晰,无炎症细胞浸润,肝细胞形态较正常,无明显肿胀。具体见图 1。
 图1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残肝的的病理学改变(HE ×100) a:A组;b:B组;c:C组;d:D组
图1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残肝的的病理学改变(HE ×100) a:A组;b:B组;c:C组;d:D组
2.4 肝细胞凋亡指数检测结果
结果见图 2 及图 3。由图 2 和图 3 可见,TUNEL染色的蓝色背景下发绿色荧光的细胞为阳性凋亡肝细胞。A、B、C 3 个组术后 1 d残肝细胞凋亡指数达到最大,而后逐渐下降;与其他 3 组比较,D组残肝细胞凋亡指数在术后各时相均为最低;如图 4 所示,术后 1 d和 2 d 4 组大鼠的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凋亡指数为 A 组>B 组>C 组>D组;术后 3 d及 6 d,除C组与D组之间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各组两两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2
示TUNEL法检测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凋亡荧光图(TUNEL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发绿色荧光者为阳性凋亡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图2
示TUNEL法检测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凋亡荧光图(TUNEL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发绿色荧光者为阳性凋亡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图3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各时相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和 2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A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B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3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各时相残肝肝细胞凋亡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和 2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A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和 6 d,B组与同时相C组及D组比较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4
示Brdu标记的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增殖情况(Brdu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呈棕染的细胞为阳性增殖肝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图4
示Brdu标记的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 1 d的残肝细胞增殖情况(Brdu ×400) 细胞质及细胞核呈棕染的细胞为阳性增殖肝细胞;a:A组;b:B组;c:C组;d:D组
2.5 肝细胞增殖指数检测结果
结果见图 4 和图 5。由图 4 和图 5 可见,Brdu增殖标记染色的细胞质或细胞核棕染的肝细胞为增殖肝细胞。在术后 1 d,C、D 2 组大鼠的肝细胞增殖达峰值,增殖指数大小为D组>C组>B组>A组,各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后 2 d,A、B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才达峰值,但 2 组间肝细胞增殖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仍明显高于A、B组,C组又明显高于其他 3 组,即A组比C组、A组比D组、B组比C组、B 组比D组和C组比D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3 d,除了C、D 2 组间肝细胞增殖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组两两间比较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6 d,A、B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无明显升高,C、D 2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明显降低,4 组的肝细胞增殖指数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图5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不同时相残肝肝细胞增殖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2 d,C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5
示各组大鼠70%肝切除术后不同时相残肝肝细胞增殖指数检测结果 *为术后 1 d,4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2 d,C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 组与同时相A组及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为术后 3 d,D组与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目前,根治性切除是肝门胆管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但由于肝门部解剖结构复杂,且肝门胆管癌极易侵犯肝门部动脉和门静脉,使得肝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较困难。尽管血管切除重建并非手术禁止,但肝门胆管癌手术时有时血管重建仍较困难,尤其是肝动脉重建[4,7-8]。若对于这部分患者,行肝动脉切除后不予以重建势必可以增加患者根治性切除的机会。但对于肝门胆管癌患者肝动脉切除后不重建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Neuhaus等[9]分析了80例行肝切除的肝门胆管癌患者资料后指出,行门静脉切除者 5 年生存率可高达65%,明显高于未行门静脉切除的28%。但de Jong等[10]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指出,虽然联合肝切除与门静脉切除可提高肝门胆管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但其早期死亡风险明显高于未行门静脉切除者。
肝脏由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供血。常规情况下,肝总动脉自腹腔干发出后,主要分出肝固有动脉和胃十二指肠动脉,肝固有动脉又依次分出胃右动脉、肝左/右动脉和胆囊动脉。肝左右动脉分支入肝后,在肝门区或肝内延着Glisson鞘多次分支并伴随门静脉和肝管分支一起走行于Glisson鞘内,形成非常丰富的动脉侧支吻合。肝脏除了常规的肝动脉供应动脉血外,在肝周韧带内还存在多条侧支循环。当肝动脉被慢性侵犯或压闭阻塞时,肝脏侧支循环就会增粗变大,供血量明显增加。Michels等[11-13]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多次研究报告了肝脏的侧支循环。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14-16]亦证实,术前若肿瘤侵犯导致肝脏动脉血供完全阻断,并不会对肝脏功能产生巨大影响。笔者此前的研究[5]亦认为,对于术中拟切除肝动脉不予重建的患者,不要游离剩余肝脏的肝周韧带,以便保存侧支循环。本研究亦证实,肝动脉结扎后将增加肝细胞凋亡,减弱肝细胞再生能力。
细胞凋亡是由特定基因控制,在酶促反应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发生的细胞主动死亡过程,是机体维持自我平衡的一种生理机制[17]。在肝细胞凋亡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正常肝脏,行70%大部肝切除后大鼠或结扎肝动脉联合肝切除的大鼠来说,70%肝切除未明显促进残肝肝细胞凋亡,但是肝动脉的结扎明显促进了术后早期(2 d内)的肝细胞凋亡;而到了晚期(3 d后),2 组大鼠残肝肝细胞的凋亡情况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脏再生是残肝肝细胞通过有丝分裂形成新的细胞,恢复原来肝细胞数量和肝体积的生理机制。有研究[18]报道,大鼠大部肝切除术后,残肝肝细胞的DNA合成在24 h内达到高峰,7~10 d残肝即再生恢复到原来的肝脏体积。研究[18]发现,肝再生主要是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刺激内皮细胞形成新生血管并刺激肝细胞增殖完成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肝再生方面,正常肝脏状态下,70%肝切除或结扎肝动脉联合70%肝切除的大鼠都会在术后 2 d内达到增殖高峰;结扎肝动脉在切除术后早期(2 d内)减弱了大部肝切除大鼠的肝脏再生能力,但同时也延长了残肝肝细胞增殖的时间;在术后 6 d时,2 组的肝脏再生已接近完成。
多数学者[19-21]认为,梗阻性黄疸状态下,肝细胞凋亡是梗阻性黄疸引起肝细胞死亡并导致肝脏损害的主要原因,所以,肝脏功能的衰竭主要是由肝细胞的凋亡引起的。肝细胞凋亡在梗阻性黄疸的肝脏病理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梗阻性黄疸过程中,高浓度的胆汁酸盐直接损害肝细胞、引起肝细胞凋亡,再加上淤胆状态下机体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和大量细胞因子的产生,加剧了肝细胞的凋亡[22-24]。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梗阻性黄疸模型大鼠实施70%肝切除联合肝动脉结扎组较70%肝切除组肝细胞凋亡增加,再生能力减弱。但 2 组的术后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同时还发现,最影响肝细胞凋亡与肝脏再生的因素是梗阻性黄疸。
综上,本研究结果证实,结扎肝动脉将增加残肝肝细胞凋亡,减弱肝细胞再生。但结扎肝动脉并未增加梗阻性黄疸大鼠术后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