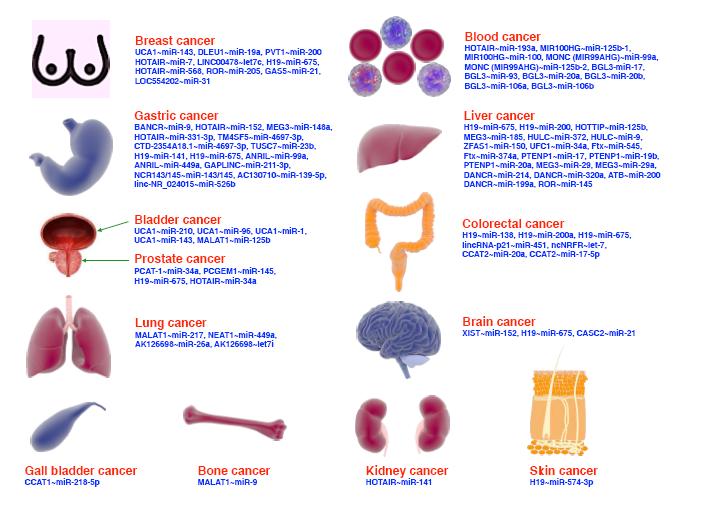引用本文: 翟惠芬, 徐波, 王浩彦. 人 β-防御素和维生素 D 在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的临床应用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8, 17(6): 629-632. doi: 10.7507/1671-6205.201803014 复制
呼吸道上皮通过呼吸过程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为了抵抗外界有害微生物入侵,人体逐渐进化出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先天性免疫系统。除物理屏障外,上皮细胞分泌大量的抗微生物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AMPs),是宿主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2],人 β-防御素(human β-defensins,hBD)是 AMPs 家族中的重要一员[3]。hBD 主要分为 1~4 型,主要来源于上皮细胞及巨噬细胞,hBD2 和 hBD3 已被证实存在于肺组织中[4-5],体外研究显示 hBD 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包膜病毒、分枝杆菌等有广谱杀菌作用[6]。hBD 的产生、调控与维生素 D(vitamin D,VD)密切相关。研究表明 VD 不仅维持骨钙代谢平衡,而且对免疫功能也有潜在益处[7]。VD 以 25(OH)D3 的形式储存在体内,当机体受到细菌入侵等外源性刺激时,1α-羟化酶 CYP27B1 将被激活,在免疫细胞、上皮细胞和非肾细胞中转化为活性形式 1,25(OH)2D3。活性 VD 的合成有利于调节免疫反应效应物质的基因表达,其中包括依赖 VD 的 AMPs[8]。这提示维持 VD 储备充足很重要,VD 缺乏将增加感染的机会[7-9]。因此,研究 hBD 和 VD 在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为感染的控制和预后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很多学者进行了该方面的研究,本文就此做一综述。
1 hBD 和 VD
1.1 hBD 的产生
病原菌入侵人体后,人体识别并迅速启动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和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产生特异性防御素蛋白,直接破坏病原体,从而抑制或杀灭入侵的病原体,目前这一过程已经基本明了[8]。病原微生物拥有相对保守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这种分子模式存在于多种微生物中,哺乳动物则缺失这种分子模式[10];哺乳动物存在的病原识别受体称钟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哺乳动物至少有 12 种不同的 TLRs,多种细胞如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上皮细胞上都有 TLRs。病原体入侵后,PAMPs 激活各种屏障和细胞膜上的 TLRs,对人类而言,TLR2/1 与革兰阳性菌细胞壁上的肽聚糖结合,TLR4 与革兰阴性菌细胞壁上的脂多糖结合。当 TLR2/1 和 TLR4 被触发时在受损局部诱导产生 CYP27B1,促进循环中的 25(OH)D3 转化为活性型 VD 即 1,25(OH)2D3。1, 25(OH)2D3 与 VD 受体及类视黄醇 X 受体结合形成复合物,之后这一复合物与 VD 响应元件结合,激活防御素基因 DEFB 的启动子,并与 NF-κB、转录因子激活蛋白(activator protein 1,AP-1)等通路的相应位点结合,继而转录、翻译,生成 hBD 防御素蛋白[2, 9, 11]。这一过程非常迅速,从识别到产生特异性防御素蛋白仅需数分钟,且不同 AMPs 之间有协同作用。防御素的失活目前研究甚少,hBD2 和 hBD3 的降解可能与弹性纤维溶解组织蛋白酶有关[2]。
1.2 hBD 的调控
hBD 的调控精密而复杂,当前研究仅为体外细胞实验。研究表明苯丁酸(phenylbutyrate,PBA)[12]、低氧[13]可通过增强 VD 的作用,上调 VD 介导的抗微生物效应通路促进 hBD 的表达,联合应用 PBA 和 VD 在体外能抑制铜绿假单胞菌的生长。慢性炎症[2]和激素[14]可下调 hBD 的表达。某些细胞因子、炎症因子也对 hBD 的产生有影响,如 CD40 配体和 γ 干扰素可诱导 CYP27B1,使 VD 转化为活性形式,上调 DEFB4/hBD2,诱导细胞自噬[15-16];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 通过 IL-1 受体 1 信号和 IL-1β 驱动上皮细胞 DEFB4/hBD2 的产生,刺激肺上皮细胞抗分枝杆菌活性,而 1,25(OH)2D3 通过直接转录机制提高了 IL-1β 的表达[17];IL-10 能抑制人胎盘细胞 DEFB 表达,而 1,25(OH)2D3 能抵消这种抑制作用[18];IL-4 单独或与 TLR2/1 一起,使 25(OH)D3 在 24-羟化酶 CYP24A1 作用下分解为无活性的 24,25(OH)2D3,从而抑制 AMPs 的表达[16]。由此可见,多种因素参与了 hBD 的调节,多数与 VD 关系密切。
防御素的产生依赖于循环中充足的 25(OH)D3,当 VD 降低时,上述调节过程异常[19],在牛乳腺内注射 1,25(OH)2D3,β-防御素基因表达增加[20]。因 hBD 在正常情况下浓度很低,而微生物刺激时高浓度诱导表达,目前尚无人体内 VD 水平与 hBD 浓度相关性的研究。
2 hBD 与 CAP
体外研究发现 hBD 直接破坏病原菌,可起到抗生素样作用,但尚无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报道。有学者研究了 hBD 在 CAP 患者中的表达、预后评价中的作用。
2.1 hBD 在 CAP 患者中的表达
Hiratsuka 等[4]首创放免法测定 hBD2,发现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浆中 hBD2 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Ishimoto 等[5]首次在呼吸系统和血清中发现 hBD3 并人工合成,发现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清 hBD3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抗生素治疗后明显下降。我国何丽蓉等[21]、刘松等[22]亦发现 CAP 患者外周血中 hBD2 浓度显著升高,且 hBD2 升高主要表现在疾病早期或相对早期。印尼 Harimurti 等[23]比较老年、青年肺炎患者呼吸道黏膜 hBD2 浓度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两组痰中 hBD2 无显著差异,营养状态、吸烟、糖尿病与 hBD2 浓度无关,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痰 hBD2 水平有关,但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尚不明确。
2.2 hBD 在评价 CAP 预后中的作用
Leow 等[24]将 30 天死亡作为研究终点,发现 hBD2 与 30 天 CAP 病死率无关,而 Liu 等[25]将 30 天不良结局作为研究终点,包括死亡、需要机械通气、出现并发症(肺炎旁胸腔积液、脓胸和肺脓肿),发现入院时较低的 hBD2 水平提示较高的不良预后发生率,30 天出现并发症和需有创通气治疗患者比例显著增多(P<0.01),30 天总病死率有增高趋势(P=0.05)。两项研究的结果不同,可能与两者研究终点不同有关。上述研究测定 hBD 的方法不同,但 hBD 在急性肺炎早期升高已基本明确。但是当前研究并未区分病原菌和是否应用抗生素,有关不同病原菌和应用抗生素对 hBD 表达的影响,hBD 在不同人群 CAP 中演变趋势及其与 CAP 预后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3 VD 与 CAP
VD 不足时,hBD 的产生受到影响,机体抵御致病原的能力下降,增加了感染的机会,这对 CAP 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预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补充 VD 后有可能对 CAP 患者有益。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涉及不同年龄段儿童和成人。
3.1 VD 与 CAP 发病风险
在儿童,多数研究表明 VD 水平降低增加肺炎发病风险。新生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ALRI)者 VD 水平明显减低,提示 VD 水平降低可能与新生儿增加的 ALRI 风险有关[26]。重症 CAP 患儿 VD 水平明显低于轻症组和对照组,VD<50 nmol/L 是重症肺炎的危险因素[27]。印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入组 960 例 6~30 月龄儿童,发现 VD 缺乏组与 VD 充足组比较,6 个月 ARLI 风险显著增加[28]。
在成人,有 3 项前瞻性研究证实 VD 水平不足可增加肺炎发生风险。芬兰 Aregbesola 等[29]利用一项缺血性心脏病危险因素研究的病例来探讨普通老年人群血清 VD 水平和发生肺炎的风险,共入组 1 421 例,随访 10 年,通过查询出院记录发现肺炎不良事件,结果在 9.8 年中 73 例至少发生 1 次肺炎;VD 浓度低三分位组发生肺炎的风险是高三分位组的 2.6 倍。哈佛大学 Quraishi 等[30]利用美国第三次健康和营养普查的数据,共有 16 975 名>17 岁的成人参与,平均 VD 水平是 24 ng/ml,2.1% 的参与者报告在普查 1 年内患 CAP,VD<30 ng/ml 发生 CAP 的风险比正常高 56%。VD 在 30 ng/ml 左右时,VD 水平与 CAP 的累积频率呈线性关系。日本 Asamura 等[31]研究发现血清 VD 不足增加健康护理机构老年人肺炎的发生风险。
3.2 VD 与 CAP 严重程度
这一方面有关成人与儿童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美国 Jovanovich 等[32]研究了急性感染之前 15 个月内 VD 水平和发生 CAP、脓毒症的风险,结果表明 VD<37 nmol/L 与 CAP 住院、脓毒症住院相关。德国 Pletz 等[33]研究了 300 例有明确病原学结果的 CAP 患者,发现 1,25(OH)2D3 水平与 CAP 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肝脏和呼吸系统并发症与低 25(OH)D3 水平相关,肾脏并发症与低 1,25(OH)2D3 水平相关,病原菌种类与 25(OH)D3 或 1,25(OH)2D3 水平无关。但一项对急性毛细支气管炎幼儿患者的研究发现 VD 水平与住院风险无关[34]。
3.3 VD 与 CAP 预后
也门 Banajeh[35]对 152 例 2~59 月龄极重症肺炎患儿的研究发现 VD 缺乏与中性粒细胞和血氧饱和度下降强相关。在成人方面,新西兰 Leow 等[24]发现 VD 缺乏与 CAP 30 天病死率有关。芬兰 Remmelts 等[36]发现 VD 缺乏是 CAP 30 天病死率的独立预测因子,VD 水平联合肺炎严重指数预测肺炎预后优于单用肺炎严重指数。韩国 Kim 等[37]发现 VD 缺乏组 28 天全因死亡率高于非 VD 缺乏组,VD 水平与 28 天全因死亡风险呈负相关。挪威 Holter 等[38]随访一项前瞻性 CAP 研究的生存病例,追踪国家死因登记的死亡数据,各种因素校正后 VD 缺乏组病死率高于 VD 充足组。上述研究均发现 VD 缺乏与不良预后有关,但 VD 缺乏的定义值不同。
3.4 VD 营养干预对 CAP 的影响
VD 对免疫系统的有益作用使得人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补充 VD 能否降低发生肺炎的风险和严重程度。目前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探究了补充 VD 对 CAP 的作用。日本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针对学龄儿童在冬季每日补充 VD,发现其降低了甲型流感及继发性肺炎的发生风险[39],而阿富汗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针对门诊 1~36 月龄肺炎儿童,双盲法给予 VD 和安慰剂,结果发现对肺炎持续时间无影响,但 90 天内肺炎复发率降低[40]。
阿富汗另一项随机对照优效试验采用每季度单次补充 VD 10 万 U 共 18 个月的方法,发现其对喀布尔婴幼儿肺炎发生率无影响[41]。印度学者对重症肺炎患儿补充 VD,病例组和对照组在重症肺炎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呼吸困难缓解时间、不能进食时间上并无显著差异[42]。英国学者分析 3 个独立的病例对照研究,校正混杂因素后,发现在成人补充 VD 和发生肺炎的风险无关[43]。
上述研究结果不完全符合预期,但年龄、人种、基础营养状态的差异,补充 VD 的方法是否符合药代动力学、补充量是否充分等因素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因此尚不能认为补充 VD 对 CAP 无益。今后还需在不同年龄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低的人群,以及有可能导致免疫效应改变的因素如基线 VD 水平、遗传变异为特点的人群中进行更频繁的给药方式研究。
4 结语
hBD 是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病原微生物入侵时在呼吸道上皮高浓度诱导表达,具有广泛而非特异的抗菌作用。hBD 在急性肺炎早期升高,但不同病原菌和应用抗生素对 hBD 表达是否有影响以及 hBD 与 CAP 预后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VD 对 hBD 的产生和调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体内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通过研究 VD 在 CAP 中的作用,发现 VD 在预测 CAP 的发生风险、严重程度和预后方面有一定价值,营养干预可能对 CAP 患者有益。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研究区分人群对给药方法进行探索。
呼吸道上皮通过呼吸过程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为了抵抗外界有害微生物入侵,人体逐渐进化出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先天性免疫系统。除物理屏障外,上皮细胞分泌大量的抗微生物肽(antimicrobial peptides,AMPs),是宿主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2],人 β-防御素(human β-defensins,hBD)是 AMPs 家族中的重要一员[3]。hBD 主要分为 1~4 型,主要来源于上皮细胞及巨噬细胞,hBD2 和 hBD3 已被证实存在于肺组织中[4-5],体外研究显示 hBD 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包膜病毒、分枝杆菌等有广谱杀菌作用[6]。hBD 的产生、调控与维生素 D(vitamin D,VD)密切相关。研究表明 VD 不仅维持骨钙代谢平衡,而且对免疫功能也有潜在益处[7]。VD 以 25(OH)D3 的形式储存在体内,当机体受到细菌入侵等外源性刺激时,1α-羟化酶 CYP27B1 将被激活,在免疫细胞、上皮细胞和非肾细胞中转化为活性形式 1,25(OH)2D3。活性 VD 的合成有利于调节免疫反应效应物质的基因表达,其中包括依赖 VD 的 AMPs[8]。这提示维持 VD 储备充足很重要,VD 缺乏将增加感染的机会[7-9]。因此,研究 hBD 和 VD 在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为感染的控制和预后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很多学者进行了该方面的研究,本文就此做一综述。
1 hBD 和 VD
1.1 hBD 的产生
病原菌入侵人体后,人体识别并迅速启动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和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产生特异性防御素蛋白,直接破坏病原体,从而抑制或杀灭入侵的病原体,目前这一过程已经基本明了[8]。病原微生物拥有相对保守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这种分子模式存在于多种微生物中,哺乳动物则缺失这种分子模式[10];哺乳动物存在的病原识别受体称钟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哺乳动物至少有 12 种不同的 TLRs,多种细胞如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上皮细胞上都有 TLRs。病原体入侵后,PAMPs 激活各种屏障和细胞膜上的 TLRs,对人类而言,TLR2/1 与革兰阳性菌细胞壁上的肽聚糖结合,TLR4 与革兰阴性菌细胞壁上的脂多糖结合。当 TLR2/1 和 TLR4 被触发时在受损局部诱导产生 CYP27B1,促进循环中的 25(OH)D3 转化为活性型 VD 即 1,25(OH)2D3。1, 25(OH)2D3 与 VD 受体及类视黄醇 X 受体结合形成复合物,之后这一复合物与 VD 响应元件结合,激活防御素基因 DEFB 的启动子,并与 NF-κB、转录因子激活蛋白(activator protein 1,AP-1)等通路的相应位点结合,继而转录、翻译,生成 hBD 防御素蛋白[2, 9, 11]。这一过程非常迅速,从识别到产生特异性防御素蛋白仅需数分钟,且不同 AMPs 之间有协同作用。防御素的失活目前研究甚少,hBD2 和 hBD3 的降解可能与弹性纤维溶解组织蛋白酶有关[2]。
1.2 hBD 的调控
hBD 的调控精密而复杂,当前研究仅为体外细胞实验。研究表明苯丁酸(phenylbutyrate,PBA)[12]、低氧[13]可通过增强 VD 的作用,上调 VD 介导的抗微生物效应通路促进 hBD 的表达,联合应用 PBA 和 VD 在体外能抑制铜绿假单胞菌的生长。慢性炎症[2]和激素[14]可下调 hBD 的表达。某些细胞因子、炎症因子也对 hBD 的产生有影响,如 CD40 配体和 γ 干扰素可诱导 CYP27B1,使 VD 转化为活性形式,上调 DEFB4/hBD2,诱导细胞自噬[15-16];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 通过 IL-1 受体 1 信号和 IL-1β 驱动上皮细胞 DEFB4/hBD2 的产生,刺激肺上皮细胞抗分枝杆菌活性,而 1,25(OH)2D3 通过直接转录机制提高了 IL-1β 的表达[17];IL-10 能抑制人胎盘细胞 DEFB 表达,而 1,25(OH)2D3 能抵消这种抑制作用[18];IL-4 单独或与 TLR2/1 一起,使 25(OH)D3 在 24-羟化酶 CYP24A1 作用下分解为无活性的 24,25(OH)2D3,从而抑制 AMPs 的表达[16]。由此可见,多种因素参与了 hBD 的调节,多数与 VD 关系密切。
防御素的产生依赖于循环中充足的 25(OH)D3,当 VD 降低时,上述调节过程异常[19],在牛乳腺内注射 1,25(OH)2D3,β-防御素基因表达增加[20]。因 hBD 在正常情况下浓度很低,而微生物刺激时高浓度诱导表达,目前尚无人体内 VD 水平与 hBD 浓度相关性的研究。
2 hBD 与 CAP
体外研究发现 hBD 直接破坏病原菌,可起到抗生素样作用,但尚无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报道。有学者研究了 hBD 在 CAP 患者中的表达、预后评价中的作用。
2.1 hBD 在 CAP 患者中的表达
Hiratsuka 等[4]首创放免法测定 hBD2,发现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浆中 hBD2 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Ishimoto 等[5]首次在呼吸系统和血清中发现 hBD3 并人工合成,发现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清 hBD3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抗生素治疗后明显下降。我国何丽蓉等[21]、刘松等[22]亦发现 CAP 患者外周血中 hBD2 浓度显著升高,且 hBD2 升高主要表现在疾病早期或相对早期。印尼 Harimurti 等[23]比较老年、青年肺炎患者呼吸道黏膜 hBD2 浓度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两组痰中 hBD2 无显著差异,营养状态、吸烟、糖尿病与 hBD2 浓度无关,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痰 hBD2 水平有关,但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尚不明确。
2.2 hBD 在评价 CAP 预后中的作用
Leow 等[24]将 30 天死亡作为研究终点,发现 hBD2 与 30 天 CAP 病死率无关,而 Liu 等[25]将 30 天不良结局作为研究终点,包括死亡、需要机械通气、出现并发症(肺炎旁胸腔积液、脓胸和肺脓肿),发现入院时较低的 hBD2 水平提示较高的不良预后发生率,30 天出现并发症和需有创通气治疗患者比例显著增多(P<0.01),30 天总病死率有增高趋势(P=0.05)。两项研究的结果不同,可能与两者研究终点不同有关。上述研究测定 hBD 的方法不同,但 hBD 在急性肺炎早期升高已基本明确。但是当前研究并未区分病原菌和是否应用抗生素,有关不同病原菌和应用抗生素对 hBD 表达的影响,hBD 在不同人群 CAP 中演变趋势及其与 CAP 预后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3 VD 与 CAP
VD 不足时,hBD 的产生受到影响,机体抵御致病原的能力下降,增加了感染的机会,这对 CAP 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预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补充 VD 后有可能对 CAP 患者有益。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涉及不同年龄段儿童和成人。
3.1 VD 与 CAP 发病风险
在儿童,多数研究表明 VD 水平降低增加肺炎发病风险。新生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ALRI)者 VD 水平明显减低,提示 VD 水平降低可能与新生儿增加的 ALRI 风险有关[26]。重症 CAP 患儿 VD 水平明显低于轻症组和对照组,VD<50 nmol/L 是重症肺炎的危险因素[27]。印度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入组 960 例 6~30 月龄儿童,发现 VD 缺乏组与 VD 充足组比较,6 个月 ARLI 风险显著增加[28]。
在成人,有 3 项前瞻性研究证实 VD 水平不足可增加肺炎发生风险。芬兰 Aregbesola 等[29]利用一项缺血性心脏病危险因素研究的病例来探讨普通老年人群血清 VD 水平和发生肺炎的风险,共入组 1 421 例,随访 10 年,通过查询出院记录发现肺炎不良事件,结果在 9.8 年中 73 例至少发生 1 次肺炎;VD 浓度低三分位组发生肺炎的风险是高三分位组的 2.6 倍。哈佛大学 Quraishi 等[30]利用美国第三次健康和营养普查的数据,共有 16 975 名>17 岁的成人参与,平均 VD 水平是 24 ng/ml,2.1% 的参与者报告在普查 1 年内患 CAP,VD<30 ng/ml 发生 CAP 的风险比正常高 56%。VD 在 30 ng/ml 左右时,VD 水平与 CAP 的累积频率呈线性关系。日本 Asamura 等[31]研究发现血清 VD 不足增加健康护理机构老年人肺炎的发生风险。
3.2 VD 与 CAP 严重程度
这一方面有关成人与儿童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美国 Jovanovich 等[32]研究了急性感染之前 15 个月内 VD 水平和发生 CAP、脓毒症的风险,结果表明 VD<37 nmol/L 与 CAP 住院、脓毒症住院相关。德国 Pletz 等[33]研究了 300 例有明确病原学结果的 CAP 患者,发现 1,25(OH)2D3 水平与 CAP 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肝脏和呼吸系统并发症与低 25(OH)D3 水平相关,肾脏并发症与低 1,25(OH)2D3 水平相关,病原菌种类与 25(OH)D3 或 1,25(OH)2D3 水平无关。但一项对急性毛细支气管炎幼儿患者的研究发现 VD 水平与住院风险无关[34]。
3.3 VD 与 CAP 预后
也门 Banajeh[35]对 152 例 2~59 月龄极重症肺炎患儿的研究发现 VD 缺乏与中性粒细胞和血氧饱和度下降强相关。在成人方面,新西兰 Leow 等[24]发现 VD 缺乏与 CAP 30 天病死率有关。芬兰 Remmelts 等[36]发现 VD 缺乏是 CAP 30 天病死率的独立预测因子,VD 水平联合肺炎严重指数预测肺炎预后优于单用肺炎严重指数。韩国 Kim 等[37]发现 VD 缺乏组 28 天全因死亡率高于非 VD 缺乏组,VD 水平与 28 天全因死亡风险呈负相关。挪威 Holter 等[38]随访一项前瞻性 CAP 研究的生存病例,追踪国家死因登记的死亡数据,各种因素校正后 VD 缺乏组病死率高于 VD 充足组。上述研究均发现 VD 缺乏与不良预后有关,但 VD 缺乏的定义值不同。
3.4 VD 营养干预对 CAP 的影响
VD 对免疫系统的有益作用使得人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补充 VD 能否降低发生肺炎的风险和严重程度。目前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探究了补充 VD 对 CAP 的作用。日本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针对学龄儿童在冬季每日补充 VD,发现其降低了甲型流感及继发性肺炎的发生风险[39],而阿富汗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针对门诊 1~36 月龄肺炎儿童,双盲法给予 VD 和安慰剂,结果发现对肺炎持续时间无影响,但 90 天内肺炎复发率降低[40]。
阿富汗另一项随机对照优效试验采用每季度单次补充 VD 10 万 U 共 18 个月的方法,发现其对喀布尔婴幼儿肺炎发生率无影响[41]。印度学者对重症肺炎患儿补充 VD,病例组和对照组在重症肺炎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呼吸困难缓解时间、不能进食时间上并无显著差异[42]。英国学者分析 3 个独立的病例对照研究,校正混杂因素后,发现在成人补充 VD 和发生肺炎的风险无关[43]。
上述研究结果不完全符合预期,但年龄、人种、基础营养状态的差异,补充 VD 的方法是否符合药代动力学、补充量是否充分等因素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因此尚不能认为补充 VD 对 CAP 无益。今后还需在不同年龄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低的人群,以及有可能导致免疫效应改变的因素如基线 VD 水平、遗传变异为特点的人群中进行更频繁的给药方式研究。
4 结语
hBD 是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病原微生物入侵时在呼吸道上皮高浓度诱导表达,具有广泛而非特异的抗菌作用。hBD 在急性肺炎早期升高,但不同病原菌和应用抗生素对 hBD 表达是否有影响以及 hBD 与 CAP 预后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VD 对 hBD 的产生和调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体内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通过研究 VD 在 CAP 中的作用,发现 VD 在预测 CAP 的发生风险、严重程度和预后方面有一定价值,营养干预可能对 CAP 患者有益。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研究区分人群对给药方法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