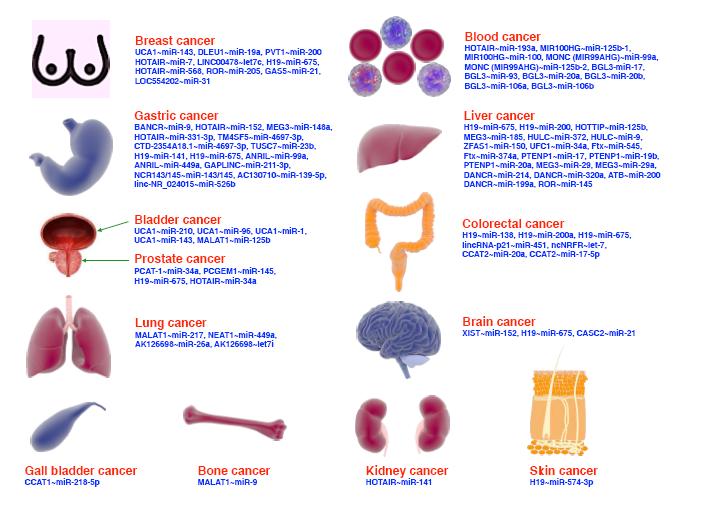本文围绕抗病毒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开展的临床研究、系统评价和指南入手,从三个维度:临床理论效力研究(efficacy)、循证临床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临床实际效果研究(effectiveness)和五个环节:研究假设、研究证据、健康医疗大数据、真实世界数据、真实世界证据,来阐述高效运行的“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进而总结当前证据生产、转化和应用当中的经验,最终为我国临床医生在循证医学理念指导下开展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引用本文: 周奇, 董冲亚, 王业明, 张博恒, 陈耀龙, 姚晨. 循证医学理念在指导临床研究与实践中的作用:基于对抗病毒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思考.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2, 22(4): 373-379. doi: 10.7507/1672-2531.202112143 复制
自1991年循证医学的理念首次提出,距今已整整30年[1-2]。在包括系统评价、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分级、报告规范和临床实践指南等领域取得了系列进展[3],但在指导具体临床实践中,循证医学的观念仍有所欠缺,未接受良好循证医学训练的医务人员过分依赖个人经验的情况仍较为普遍。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为例[4],截至2021年10月31日,全球在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等领域开展了3 000余个临床试验,合成了8 000余个系统评价/Meta分析,制订了200余部临床实践指南[5-8]。但由于大部分临床试验、系统评价/Meta分析和临床实践指南未提前统一管理和规划、方法学设计有缺陷、实施过程不严格、报告内容不规范等,导致大量研究和指南的质量低下,无法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造成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9-13]。
本文将从证据生态系统的视角,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当前证据生产和转化中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证据转化的新模型,以期为我国开展高水平循证临床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证据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抗新冠病毒药物
2017年9月,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全球循证高峰论坛(Global Evidence Summit,GES)提出了“证据生态系统(evidence ecosystem)”的概念—该系统要求打通证据生产、合成、传播和实施的壁垒,加速各环节之间的循环,形成动态、可持续的生态[14-18]。
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证据生态系统,我们将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抗病毒药物为例进行分析。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初期,有超过10余种抗病毒药物用于该疾病的治疗[19-20]。其中瑞德西韦(remdesivir,GS-5734)受到的关注度最高,与其相关的临床研究、系统评价/Meta分析和临床实践指南的数量迅速增多。截至目前共有5个组织开展了6个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21-26](表1);这些RCT被纳入到20多个系统评价中,但由于纳入研究数量及分析角度的影响,系统评价结论也不尽相同;此外,共有8个组织制订了8个有关瑞德西韦临床实践指南[27-35],但证据方向和强度也不一致(表2)。尽管证据生态系统为如何生产和转化证据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就瑞德西韦而言,临床证据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并不畅通。具体表现在:临床研究的开展缺乏严谨的设计和规范的报告,系统评价更是大量无序地制作,指南的质量良莠不齐,不同指南的推荐意见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如果我们无法成立一个跨学科的协作组织,无法从研究注册开始就对证据的生产进行管理和协调,无法对临床的原始数据进行更加系统的分析(譬如单病例的Meta分析),无法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包括卫生政策、医疗资源、患者意愿等)进行全面考量,我们就很难发现研究的真相,落地循证决策和实践。
2 对“证据生态系统”的思考及“3E”证据转化模型的探索
虽然基于RCT的疗效证据被认为是循证医学中验证疗效的金标准,但其并不适合所有的临床情景。真实世界数据(real world data,RWD)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35],近年来,该理念和方法在国内外得以快速发展[36-40]。根据上述“证据生态系统”的理念,本文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的开展、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RWS)效果评价三个方面,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证据转化模型,即“单一干预措施的理论效力评价的临床试验(efficacy)、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临床实际效果的RWS(effectiveness)”(下文简称“3E”模型)。该模型由5个具体环节组成,分别为研究假设、研究证据、健康医疗大数据、RWD和真实世界证据(real world evidence,RWE)(图1)。
 图1
“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
图1
“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
2.1 凝练科学问题,提出研究假设
COVID-19世界大流行期间,及早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重症率、病死率是临床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临床需求)。COVID-19是由SARS-CoV-2病毒感染人体所致,针对病毒的抗病毒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否有益(临床问题)?通过梳理临床现有抗病毒药物,发现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的瑞德西韦(属于核苷前体类广谱抗病毒药物),可能是治疗COVID-19最有潜力的抗病毒药物之一[40]。提出“瑞德西韦可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研究假设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① 非人体实验的间接证据表明瑞德西韦在体外实验及冠状病毒动物模型中具有强效的抗病毒效果[41-43];②Ⅰ期临床试验及美国卫生研究所发起的关于瑞德西韦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Ⅱ期临床试验均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44-45];③ 临床真实世界的疗效探索试验表明瑞德西韦可能有一定的疗效:2020年1月3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首篇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病例报告,患者第7天晚上接受了瑞德西韦的静脉输注,而第8天这例患者的临床症状出现了改善,除了干咳和流鼻涕外,已无其他症状[1]。由上述过程我们可看到演绎逻辑的过程:① 瑞德西韦对目前已知的所有冠状病毒均有效(大前提);② 新型冠状病毒是冠状病毒的一种(小前提);③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表明瑞德西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有一定疗效(结论)。但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病毒感染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基于科学、规范的临床科研方法学设计,结合恰当的统计学方法指导下开展的临床试验可精确定量评价某单一治疗措施的的理论效应。因此,生产证据阶段的过程可总结为:我们需要针对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充分应用已有的条件和知识建立可靠合理的假设,并开展临床试验验证我们的假设。
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物的研发过程中,提出准确和重要的研究假设是“3E”模型的前提。基于瑞德西韦临床问题的提出可知,重要研究假设的提出需要对此前已发表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进行系统回顾,基于已知条件,通过合理的推理产生针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假设[46]。
2.2 设计和实施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据
重要的临床问题提出后,可采用的临床研究方法众多(例如RCT、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研究等),且均能在不同程度验证干预措施的疗效,为临床问题提供一定的研究证据。但是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研究等观察性研究结果往往受到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未有效控制混杂因素)所限,无法给出强有力“理论效力”的论证依据[5],因此,作为临床研究中证据水平最高、论证干预措施“理论效力”最好的RCT,其充分平衡了除干预措施外的其他因素作用,加之盲法评价减少了试验过程中的信息偏倚,与对照组相比可精确定量干预措施“效应大小”,在此次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研究过程中被临床研究者所推崇。由表1可知,中国、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依次开展6个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RCT[21-26]来论证“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是否具有良好的效果和安全性”这一研究假设。
因此,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条件和客观环境,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同时需要充分认识所产生的研究证据等级。新冠疫情期间,研究者曾提出非常多的研究假设,诸如羟氯喹、阿奇霉素、秋水仙碱及干扰素等治疗COVID-19的研究假设,部分回顾性的观察性临床研究也支持初步的研究假设,但最终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上述药物均对COVID-19无效,甚至有毒副作用。
2.3 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
针对相同的临床问题,常常因研究开展过程时招募的人群、对照措施的选择、结局指标的设定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产生不同研究结果的临床研究证据(例如,表1汇总的6个瑞德西韦RCT中,因纳入人群的严重程度、常规治疗措施的实施、有效率结局指标的定义不同,最终关于“瑞德西韦是否有效”的高质量RCT研究结果之间有所差异)。临床医生如果仅片面地基于单篇研究的结果进行临床实践,常会导致做出偏倚甚至有害的临床决策。因此,在应用临床证据进行医疗实践的环节中,生产出来的研究证据是不能直接转化为临床实践过程的指导意见,需要在循证医学理念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不同的研究证据进行合理的合成与转化,从而客观地给出科学有效的临床诊疗建议。
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要求临床医生依靠自身的临床经验,结合患者意愿,充分参考系统评价合成的临床研究证据,做出有效合理的临床决策[3-5],而其中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则是实现这一科学决策的重要桥梁[47]。虽然有时指南采纳的临床研究证据源人群与医疗实践中的真实人群可能存在差距,甚至可能无法回答对临床实践中碰到的复杂患者或单个患者多种疾病共患的临床难题[48]。在无指南可用或指南不能够回答临床问题时,临床医生可按照系统评价/Meta分析的方法,总结应用当前最佳证据[49]。譬如,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循证医疗实践中,前期有6个RCT发表,但结论不一致;后来针对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发表了相关的系统评价。基于系统评价证据,WHO等机构(表2)进而发布了指导临床医生进行医疗实践的COVID-19动态指南[27-34]。当然除了上述的情况外,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早期或罕见病领域)缺乏直接研究证据支持时,临床医生甚至可基于“专家意见”进行“当前最佳”的临床实践[50]。
2.4 RWD与证据
基于RCT得出的临床研究证据,只给出了干预措施在理想状态下的内部真实性结果,对复杂多变的临床诊疗环境,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是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因此,基于汇总的临床研究证据做好循证临床实践,是需要在复杂多变的临床诊疗环境中验证干预措施的外部真实性,对真实诊疗环境中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可验证我们临床决策(研究假设)的实际效果,这个过程本质上即为RWS[51]。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RWS并不意味着观察性研究,因在真实医疗环境下仍然能开展试验性研究(如实效性RCT)。真实的诊疗环境下会产生大量的医疗数据,根据研究目的制定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开展RWS的研究设计方案,确定RWD采集、治理和适用性评估,通过合适的研究方法可以对真实医疗实践下的干预措施进行“实际效果”的科学性评价,从而获得相应的RWE。因此,近些年来如何有效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来验证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物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RWS被大家所关注[52-54]。RWS也广泛用于医疗产品的上市后研究,关注效果研究,即评价药物或医疗器械在真实医疗环境下的治疗效果,重在外部有效性[55]。
2020年10月22日,美国FDA正式批准瑞德西韦用于治疗需要住院的成人和青少年(12岁以上,体重≥40 kg)COVID-19患者,成为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的COVID-19治疗药物[56]。此后,瑞德西韦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RWS,例如美国Premier Healthcare Database、Aetion and HealthVerity Analysis、SIMPLE-Severe3个著名的RWS[57-60]。2021年6月21日,在世界微生物论坛中,吉利德公司基于上述3个数据库收集的98 654例COVID-19住院患者的RWD进行了再次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瑞德西韦的使用可降低23%的死亡风险[RR=0.77,95%CI(0.73,0.81)][60]。由此可见,RWE也可回答科学问题,用于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评价,是对先前获得的临床试验证据的补充完善。同时在临床实践经验及RWE积累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研究问题及假设,衍生后续的临床研究,并获得新的证据。至此,上文所述的“3E”模型及五个环节得以形成良性循环。
3 小结
“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动态循环的,并不是说整个循环的过程都必须从研究假设开始到RWS结束。如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的提出,很多情况下是基于临床医生在真实的诊疗环境中产生的大量RWD所提出来的,因为临床医生通过真实的医疗大数据发现、总结出某种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为验证假设真伪而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RWS不仅能验证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更能为临床研究假设的提出提供重要支持,因此整个循环也是可从RWS开始,从而触发后续研究假设等环节的开展。
为更好地理解“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本文以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研究为实例,对“3E”模型中的证据生产、转化和应用的5个环节进行了系统阐述。首先,基于瑞德西韦治疗冠状病毒的RWD为“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有效”这一研究假设的提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提出研究假设)。然后,为验证上述的研究假设,全球各个国家分别开展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RCT(生产研究证据)。其次,临床医生专家团队在循证医学理念的指导下,将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研究证据转化为指导医学实践的临床诊疗指南,如WHO等机构COVID-19动态指南的发布(转化研究证据)。最后,在这些临床诊疗指南更为广泛地被临床医生所采纳后,在真实的临床医疗环境中产生了大量的医疗数据。正如美国形成的Premier Healthcare Database、Aetion and HealthVerity Analysis、SIMPLE-Severe三个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RWS,给出了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实际效果”(应用研究证据)。
开展临床研究和进行临床实践是个复杂而又系统化的工程,要确保“3E”模型的高效运作,需要多学科、多专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注重临床与方法学层面的协同合作。新方法、新技术和新药物的研发,需要通过高质量的RCT进行验证,而生产出来的临床研究证据需要通过系统评价和临床实践指南这一桥梁转化为临床实践可操作的执行意见,最终在真实的医疗环境中实施,通过RWS所获得的RWE,进一步提示新的研究假设(不同角度的疗效获益、扩大人群、扩大适用范围等),让更多的临床医师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研究,为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提供最佳的证据。
利益声明 所有人员均声明不存在任何与本文相关的利益冲突。
致谢 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彭晓霞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自1991年循证医学的理念首次提出,距今已整整30年[1-2]。在包括系统评价、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分级、报告规范和临床实践指南等领域取得了系列进展[3],但在指导具体临床实践中,循证医学的观念仍有所欠缺,未接受良好循证医学训练的医务人员过分依赖个人经验的情况仍较为普遍。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为例[4],截至2021年10月31日,全球在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等领域开展了3 000余个临床试验,合成了8 000余个系统评价/Meta分析,制订了200余部临床实践指南[5-8]。但由于大部分临床试验、系统评价/Meta分析和临床实践指南未提前统一管理和规划、方法学设计有缺陷、实施过程不严格、报告内容不规范等,导致大量研究和指南的质量低下,无法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造成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9-13]。
本文将从证据生态系统的视角,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当前证据生产和转化中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证据转化的新模型,以期为我国开展高水平循证临床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证据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抗新冠病毒药物
2017年9月,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全球循证高峰论坛(Global Evidence Summit,GES)提出了“证据生态系统(evidence ecosystem)”的概念—该系统要求打通证据生产、合成、传播和实施的壁垒,加速各环节之间的循环,形成动态、可持续的生态[14-18]。
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证据生态系统,我们将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抗病毒药物为例进行分析。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初期,有超过10余种抗病毒药物用于该疾病的治疗[19-20]。其中瑞德西韦(remdesivir,GS-5734)受到的关注度最高,与其相关的临床研究、系统评价/Meta分析和临床实践指南的数量迅速增多。截至目前共有5个组织开展了6个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21-26](表1);这些RCT被纳入到20多个系统评价中,但由于纳入研究数量及分析角度的影响,系统评价结论也不尽相同;此外,共有8个组织制订了8个有关瑞德西韦临床实践指南[27-35],但证据方向和强度也不一致(表2)。尽管证据生态系统为如何生产和转化证据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就瑞德西韦而言,临床证据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并不畅通。具体表现在:临床研究的开展缺乏严谨的设计和规范的报告,系统评价更是大量无序地制作,指南的质量良莠不齐,不同指南的推荐意见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如果我们无法成立一个跨学科的协作组织,无法从研究注册开始就对证据的生产进行管理和协调,无法对临床的原始数据进行更加系统的分析(譬如单病例的Meta分析),无法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包括卫生政策、医疗资源、患者意愿等)进行全面考量,我们就很难发现研究的真相,落地循证决策和实践。
2 对“证据生态系统”的思考及“3E”证据转化模型的探索
虽然基于RCT的疗效证据被认为是循证医学中验证疗效的金标准,但其并不适合所有的临床情景。真实世界数据(real world data,RWD)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35],近年来,该理念和方法在国内外得以快速发展[36-40]。根据上述“证据生态系统”的理念,本文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的开展、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RWS)效果评价三个方面,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证据转化模型,即“单一干预措施的理论效力评价的临床试验(efficacy)、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临床实际效果的RWS(effectiveness)”(下文简称“3E”模型)。该模型由5个具体环节组成,分别为研究假设、研究证据、健康医疗大数据、RWD和真实世界证据(real world evidence,RWE)(图1)。
 图1
“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
图1
“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
2.1 凝练科学问题,提出研究假设
COVID-19世界大流行期间,及早找到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重症率、病死率是临床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临床需求)。COVID-19是由SARS-CoV-2病毒感染人体所致,针对病毒的抗病毒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否有益(临床问题)?通过梳理临床现有抗病毒药物,发现由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的瑞德西韦(属于核苷前体类广谱抗病毒药物),可能是治疗COVID-19最有潜力的抗病毒药物之一[40]。提出“瑞德西韦可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研究假设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① 非人体实验的间接证据表明瑞德西韦在体外实验及冠状病毒动物模型中具有强效的抗病毒效果[41-43];②Ⅰ期临床试验及美国卫生研究所发起的关于瑞德西韦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Ⅱ期临床试验均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44-45];③ 临床真实世界的疗效探索试验表明瑞德西韦可能有一定的疗效:2020年1月3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首篇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病例报告,患者第7天晚上接受了瑞德西韦的静脉输注,而第8天这例患者的临床症状出现了改善,除了干咳和流鼻涕外,已无其他症状[1]。由上述过程我们可看到演绎逻辑的过程:① 瑞德西韦对目前已知的所有冠状病毒均有效(大前提);② 新型冠状病毒是冠状病毒的一种(小前提);③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表明瑞德西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有一定疗效(结论)。但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病毒感染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基于科学、规范的临床科研方法学设计,结合恰当的统计学方法指导下开展的临床试验可精确定量评价某单一治疗措施的的理论效应。因此,生产证据阶段的过程可总结为:我们需要针对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充分应用已有的条件和知识建立可靠合理的假设,并开展临床试验验证我们的假设。
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物的研发过程中,提出准确和重要的研究假设是“3E”模型的前提。基于瑞德西韦临床问题的提出可知,重要研究假设的提出需要对此前已发表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进行系统回顾,基于已知条件,通过合理的推理产生针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假设[46]。
2.2 设计和实施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据
重要的临床问题提出后,可采用的临床研究方法众多(例如RCT、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研究等),且均能在不同程度验证干预措施的疗效,为临床问题提供一定的研究证据。但是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研究等观察性研究结果往往受到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未有效控制混杂因素)所限,无法给出强有力“理论效力”的论证依据[5],因此,作为临床研究中证据水平最高、论证干预措施“理论效力”最好的RCT,其充分平衡了除干预措施外的其他因素作用,加之盲法评价减少了试验过程中的信息偏倚,与对照组相比可精确定量干预措施“效应大小”,在此次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研究过程中被临床研究者所推崇。由表1可知,中国、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依次开展6个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RCT[21-26]来论证“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是否具有良好的效果和安全性”这一研究假设。
因此,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条件和客观环境,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同时需要充分认识所产生的研究证据等级。新冠疫情期间,研究者曾提出非常多的研究假设,诸如羟氯喹、阿奇霉素、秋水仙碱及干扰素等治疗COVID-19的研究假设,部分回顾性的观察性临床研究也支持初步的研究假设,但最终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上述药物均对COVID-19无效,甚至有毒副作用。
2.3 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
针对相同的临床问题,常常因研究开展过程时招募的人群、对照措施的选择、结局指标的设定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产生不同研究结果的临床研究证据(例如,表1汇总的6个瑞德西韦RCT中,因纳入人群的严重程度、常规治疗措施的实施、有效率结局指标的定义不同,最终关于“瑞德西韦是否有效”的高质量RCT研究结果之间有所差异)。临床医生如果仅片面地基于单篇研究的结果进行临床实践,常会导致做出偏倚甚至有害的临床决策。因此,在应用临床证据进行医疗实践的环节中,生产出来的研究证据是不能直接转化为临床实践过程的指导意见,需要在循证医学理念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不同的研究证据进行合理的合成与转化,从而客观地给出科学有效的临床诊疗建议。
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要求临床医生依靠自身的临床经验,结合患者意愿,充分参考系统评价合成的临床研究证据,做出有效合理的临床决策[3-5],而其中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则是实现这一科学决策的重要桥梁[47]。虽然有时指南采纳的临床研究证据源人群与医疗实践中的真实人群可能存在差距,甚至可能无法回答对临床实践中碰到的复杂患者或单个患者多种疾病共患的临床难题[48]。在无指南可用或指南不能够回答临床问题时,临床医生可按照系统评价/Meta分析的方法,总结应用当前最佳证据[49]。譬如,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循证医疗实践中,前期有6个RCT发表,但结论不一致;后来针对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发表了相关的系统评价。基于系统评价证据,WHO等机构(表2)进而发布了指导临床医生进行医疗实践的COVID-19动态指南[27-34]。当然除了上述的情况外,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早期或罕见病领域)缺乏直接研究证据支持时,临床医生甚至可基于“专家意见”进行“当前最佳”的临床实践[50]。
2.4 RWD与证据
基于RCT得出的临床研究证据,只给出了干预措施在理想状态下的内部真实性结果,对复杂多变的临床诊疗环境,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是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因此,基于汇总的临床研究证据做好循证临床实践,是需要在复杂多变的临床诊疗环境中验证干预措施的外部真实性,对真实诊疗环境中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可验证我们临床决策(研究假设)的实际效果,这个过程本质上即为RWS[51]。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RWS并不意味着观察性研究,因在真实医疗环境下仍然能开展试验性研究(如实效性RCT)。真实的诊疗环境下会产生大量的医疗数据,根据研究目的制定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开展RWS的研究设计方案,确定RWD采集、治理和适用性评估,通过合适的研究方法可以对真实医疗实践下的干预措施进行“实际效果”的科学性评价,从而获得相应的RWE。因此,近些年来如何有效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来验证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物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RWS被大家所关注[52-54]。RWS也广泛用于医疗产品的上市后研究,关注效果研究,即评价药物或医疗器械在真实医疗环境下的治疗效果,重在外部有效性[55]。
2020年10月22日,美国FDA正式批准瑞德西韦用于治疗需要住院的成人和青少年(12岁以上,体重≥40 kg)COVID-19患者,成为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的COVID-19治疗药物[56]。此后,瑞德西韦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RWS,例如美国Premier Healthcare Database、Aetion and HealthVerity Analysis、SIMPLE-Severe3个著名的RWS[57-60]。2021年6月21日,在世界微生物论坛中,吉利德公司基于上述3个数据库收集的98 654例COVID-19住院患者的RWD进行了再次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瑞德西韦的使用可降低23%的死亡风险[RR=0.77,95%CI(0.73,0.81)][60]。由此可见,RWE也可回答科学问题,用于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评价,是对先前获得的临床试验证据的补充完善。同时在临床实践经验及RWE积累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研究问题及假设,衍生后续的临床研究,并获得新的证据。至此,上文所述的“3E”模型及五个环节得以形成良性循环。
3 小结
“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是动态循环的,并不是说整个循环的过程都必须从研究假设开始到RWS结束。如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的提出,很多情况下是基于临床医生在真实的诊疗环境中产生的大量RWD所提出来的,因为临床医生通过真实的医疗大数据发现、总结出某种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为验证假设真伪而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RWS不仅能验证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更能为临床研究假设的提出提供重要支持,因此整个循环也是可从RWS开始,从而触发后续研究假设等环节的开展。
为更好地理解“3E”模型证据生态系统,本文以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研究为实例,对“3E”模型中的证据生产、转化和应用的5个环节进行了系统阐述。首先,基于瑞德西韦治疗冠状病毒的RWD为“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有效”这一研究假设的提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提出研究假设)。然后,为验证上述的研究假设,全球各个国家分别开展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RCT(生产研究证据)。其次,临床医生专家团队在循证医学理念的指导下,将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研究证据转化为指导医学实践的临床诊疗指南,如WHO等机构COVID-19动态指南的发布(转化研究证据)。最后,在这些临床诊疗指南更为广泛地被临床医生所采纳后,在真实的临床医疗环境中产生了大量的医疗数据。正如美国形成的Premier Healthcare Database、Aetion and HealthVerity Analysis、SIMPLE-Severe三个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RWS,给出了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实际效果”(应用研究证据)。
开展临床研究和进行临床实践是个复杂而又系统化的工程,要确保“3E”模型的高效运作,需要多学科、多专业人员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注重临床与方法学层面的协同合作。新方法、新技术和新药物的研发,需要通过高质量的RCT进行验证,而生产出来的临床研究证据需要通过系统评价和临床实践指南这一桥梁转化为临床实践可操作的执行意见,最终在真实的医疗环境中实施,通过RWS所获得的RWE,进一步提示新的研究假设(不同角度的疗效获益、扩大人群、扩大适用范围等),让更多的临床医师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研究,为循证医学理念下的临床实践提供最佳的证据。
利益声明 所有人员均声明不存在任何与本文相关的利益冲突。
致谢 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彭晓霞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